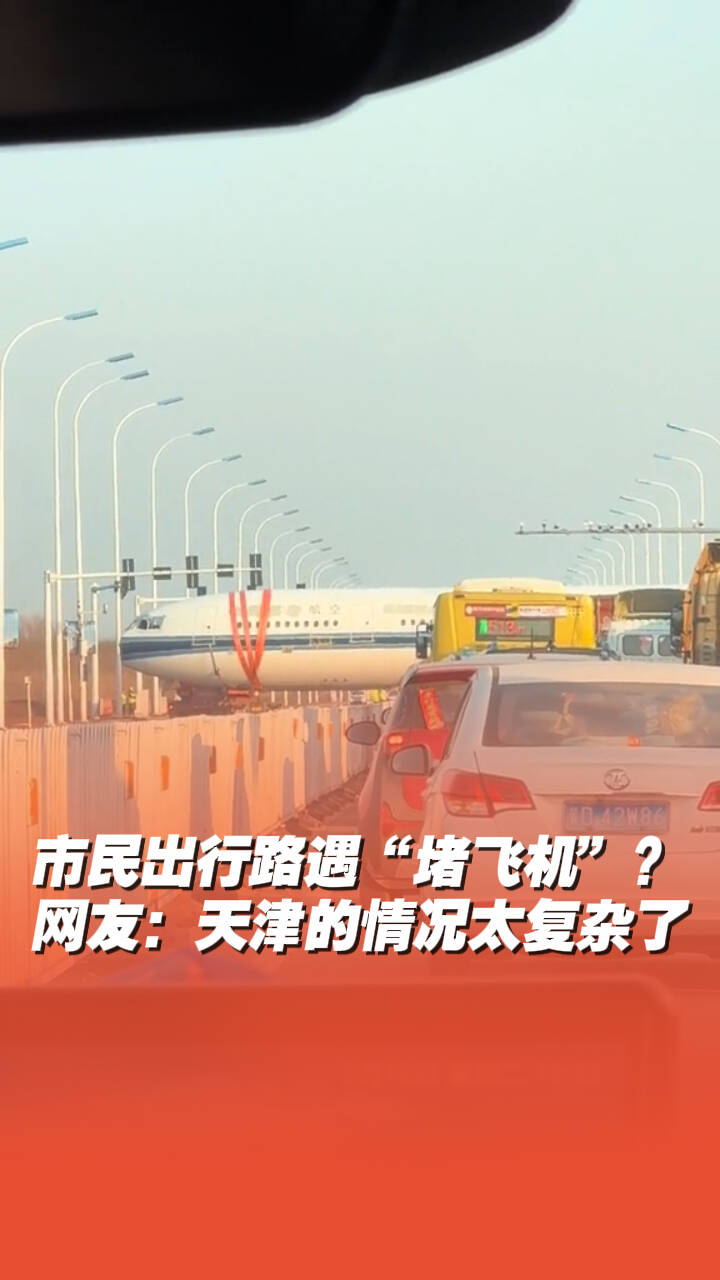我的求索之路(大家談人生)
來源:人民日報
2025-02-20 09:15:02
原標題:我的求索之路(大家談人生)
來源:人民日報
原標題:我的求索之路(大家談人生)
來源:人民日報
已走過百歲人生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
一個人的一生不能不思考到底想要做什么,立志是人一生不斷前進的動力。而志向往往并非一蹴而就,是伴隨成長的經歷、所見所聞所想一步步確立下來的。之所以選擇建筑事業作為一生的追求方向,與我青少年時的成長經歷密切相關。
我出生于國家內憂外患之際,祖國大地戰火連連,苦難深重。1937年南京淪陷,我隨家兄流亡重慶,于合川繼續中學學業。記得1940年高考結束的那天下午,合川遭遇日軍空襲,大火一直燃燒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戰亂苦痛的經歷激發了我重建家園的熱望,最終選擇進入重慶中央大學建筑系學習。
以建筑為專業,這是一個開始。隨著自己的成長,我對建筑事業發展的需求認識不斷加深,學習興趣也日益濃厚。
抗日戰爭期間,遷駐重慶沙坪壩的中央大學,一切都很簡陋。當時建筑系的系館是用毛竹捆綁的,瓦頂,籬笆墻。盡管如此,每個學生都有一塊大圖板,一張桌子,一只高腳繪圖凳。窗外俯視嘉陵江,冬季江水清碧,春來垂柳成蔭。系館門口長了些灌木,每逢初夏,梔子花開,香氣襲人……在那里,我度過兩年半的時光。往事如煙,許多事回憶起來已若隔世,但有一件事至今未能忘懷。
一年暑假,系館屋頂被暴風雨掀走,整修屋頂的工人原本歌聲不斷,但后來一位工人誤觸到高壓線,不幸身亡,屋頂上頓時沉寂。
當時,我正讀到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感到分外凄戚。房屋、歌聲、建筑工人,常常在心中串在一起,加深了我對建筑專業的情感,啟迪了我的“人居”之夢。或許這就是懵懵懂懂的逐夢人生的開始。
1945年,參加了抗日遠征軍的我又回到重慶。當時意愿很單純,就是要回去讀書。在1943年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感覺開始對建筑學開竅,寫了《釋“闕”》一文,登載在班里辦的《建筑》雜志上。回到重慶后,老學長盧繩找我,說梁思成先生希望我去見他。原來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兩位先生看到了《釋“闕”》,想找我談談。
梁先生學術視野開闊,走在時代的前面。這時期,梁先生已經開始考慮抗戰勝利后的重建工作了。我到的時候,梁先生正在讀沙里寧的《城市:它的發展、衰敗與未來》。他詢問了中央大學的教學情況,又問我是不是對中國建筑有興趣。我隨感而發,說到過西南之后有所轉變,戰爭破壞太厲害,想改為研究城市規劃。
原以為梁先生只是談談話,沒想到他明確讓我留下來,當天中午就讓我在那兒吃飯。后來我每天都去,工作了兩個多月。當時,做的事情是為梁先生的《圖像中國建筑史》進行完善。
后來,梁先生邀我去聚興村看他。梁先生說他已獲批在清華大學新辦一個建筑系,梁先生希望我去當助教。我本來也模模糊糊地想走學術道路,這令我喜出望外,立即答應了,從此開始了在清華大學70多年的教學生涯。
在清華任教期間,梁先生推薦我去美國匡溪藝術學院學習建筑與城市規劃,這是建筑師沙里寧創辦的。
沙師的教導重在啟發。他熱愛東方藝術,說這是一個寶庫,提醒我注意,不要失去東方的文化精神。匡溪的規定,學生畢業前,要舉行個展。當地的報紙將我的展品作了報道,并列出沙師的評語:“在他的工作中,灌注了一種稱之為中國現代性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來自一般的人類文化發展,而且來自中國實際生活的發展,一種新與舊的結合,基于中國自身的堅定不移的精神。”
當時,我僅僅將其理解為一般的贊勉之辭,未加多想。在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溫舊事,回顧幾十年來的道路,不就是在中與西、古與今矛盾中徘徊前進?!而什么是中國現代性的精神,如何能從中國實際的發展中發現、探索這種精神,時至今日,仍然是需要認真思考并嚴肅探討的。
闊別祖國兩年,收到一封林徽因口授、羅哲文代筆的信。大意是國內形勢很好、百廢待興,趕緊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工作。在梁林兩位先生的召喚下,我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從此開始一生為中國城鄉建設奮斗的歷程。
一個人的一生不知要走過多少“十字路口”,一個彎轉錯了就很難回到過去,因此道路的選擇至關重要。
回顧過往,有幾次重要的“十字路口”。現在想來,如果當時留在美國,便沒有此后幾十年在中國建設領域的耕耘和收獲。類似的情況一個人一生不知要經歷多少次。自我審視之所以沒有“轉錯”大方向,還是與早年“立志”相關。我很早便立志在建筑與城市的學術領域做一些事,在不同時期,根據現實條件,做出相應的選擇。
懷著心花怒放的心情,我積極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參與了長安街規劃設計、天安門廣場擴建規劃設計、毛主席紀念堂規劃設計等重大項目。
除了首都北京的規劃建設,保定城市規劃是我想特別講一講的。
保定自古即是“畿輔通衢之地”,在歷史和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開展規劃工作時,保定舊城保存尚完整,也很繁榮,是居民的主要集中地。規劃工作的任務之一是把舊城與跨過鐵路即將發展的新區聯結為一個整體。
我們對保定舊城保護、新區發展開展了全面規劃,對道路、綠地等也進行了深入設計。規劃方案不斷調整,開始新區的道路網是斜向的,后來尊重當地的意見改為正南正北,最終形成了一個比較深入而實際的規劃方案:東西城有機聯結,有廣場、有新中心、有綠帶,空間有序、疏密有致,并且對舊城的大慈閣、南大街、直隸總督署、一畝泉等處的保護也非常關注。
在數十年的學術人生中,除北京外,我參與了不少地方的規劃。但一個中等城市的規劃得以較完整付諸實踐的,唯有保定。
改革開放的洪流重新煥發了學術界的熱情。中國科學院院士(當時叫學部委員)制度恢復后,我選上了學部委員。這使我有一種強大的學術使命感,獲得了“建筑學要走向科學”的感悟。
創建建筑與城市研究所,出版《廣義建筑學》,完成菊兒胡同41號院工程,提出“人居環境科學”,主持撰寫國際建協《北京憲章》,我主要的學術成果基本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之間的近20年間完成的,很值得懷念。
我為數有限的建筑創作實踐多與文化遺產有關,菊兒胡同41號院工程比較有代表性。如何與環境保持一致?原則是“積極保護、整體創造”。
當時,41號院住了44戶人家,但只有一個水龍頭和街道公廁,人均住房面積只有5平方米左右,改建需求緊迫。
41號院的設計工作從1987年持續到1991年,十分用功。四合院的層數進行了突破,設計了2層、3層的四合院,在保證每一層都有合理日照的前提下,追求達到最高密度。樓房的四角安置樓梯,樓梯下方做開敞布局,使院落間能夠形成通風。院子里原有的兩棵古樹也保留了,周邊建筑都圍繞這兩棵古樹布局。此外,在考慮多方面限制條件的基礎上,在有限的用地面積上安置了最多的住戶,而且每家都有自己的廚房與廁所。菊兒胡同經改造最終建成后,造價控制在每平方米500元以內,我至今還保存著單據。
第一期工程完工后,獲得多方面好評,許多人認為菊兒胡同是“古都新貌”,旋即著手第二期改造工程。
1993年,菊兒胡同新四合院工程被授予“世界人居獎”,被認為“開創了在北京城中心進行城市更新的一種新的途徑”。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建筑作品首次在國際上獲取的最高榮譽。此后,我又陸續主持曲阜孔子研究院、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南京江寧織造博物館等的設計。
建筑當隨時代,我們可以從多種途徑發揮創造。作為一位中國建筑師,我深信,中國擁有深厚的建筑、風景園林和城市的文化傳統,以及豐富的東方哲學思維與美學精神。如何運用現代設計理念和技術條件,吸取多元文化內涵,探索新的形式,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這可能是避免世界文化趨同、促成當今城鄉環境豐富多彩的途徑之一。
時代需要“大科學”,也在孕育“大藝術”。2012年,因對人居環境科學的貢獻,我榮獲201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人居環境科學是隨著改革開放,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的,涉及諸多學術領域,“人居之道”是科學、人文、藝術的融匯。
未來充滿無限的生機和激情。作為一個建筑學人,畢生秉持“匠人營國”的精神,致力于“謀萬家居”的事業,這是我的“求索之路”,也是矢志不移的“中國人居夢”。拙匠邁年,豪情未已,我對“明日之人居”充滿期待!
(吳晨、郭璐整理)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提升港口智能化運營水平
- 一段時間以來,天津、遼寧等地通過采取積極舉措,努力發展港口經濟。近年來,我國港口服務能力與基礎設施水平持續提升,港口數字化智慧化轉...[詳細]
- 經濟日報 2025-02-20
為流動兒童“撐傘” 共筑溫暖成長路
-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姚建發自濟南城市和社區融入困難、監護人關愛不足、教育醫療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不足……針對流動兒童面...[詳細]
- 中國婦女報 2025-02-20
銀行業績快報陸續出爐:超八成實現營收增長
- ●本報記者吳楊A股上市銀行2024年業績快報陸續出爐。其中,超八成銀行營業收入實現同比增長;12家銀行實現營業收入、歸母凈利潤同比“雙增...[詳細]
- 中國證券報 2025-02-20
黨建引領產業興旺 蕙蘭花開香飄四方
- 近日,走進河南省洛陽市欒川縣合峪鎮蕙蘭種植基地,一盆盆蕙蘭青翠欲滴,花香四溢。基地內,養蘭能手正忙著對群眾進行種植、防蟲、防害等技...[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2-20
構建體系優化規范將“三個管理”落地落實
- 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的基礎和前提,是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一體抓實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詳細]
- 檢察日報 2025-02-20
《哪吒2》帶給公安工作的啟示
- □祝文心今年春節檔,電影《哪吒之魔童鬧海》熱映,票房不斷刷新影史紀錄。哪吒身上蘊含的維護正義、勇于擔當、敢于斗爭等諸多元素,都能在...[詳細]
- 人民公安報 2025-02-20
濱州召開電梯維保單位約談會
- 本報訊近日,山東省濱州市市場監管局組織召開電梯維保單位集中約談暨《濱州市電梯維保單位質量與安全評價管理暫行辦法》宣貫會,全面落實電...[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2-20
山東“開工第一課”護航企業復工復產
- 本報訊2月10日,山東省市場監管局開展省級特種設備安全監督檢查情況通報分析暨“開工第一課”活動,進一步做好復工復產準備工作,從嚴從實...[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2-20
山東:持續深入打好藍天、碧水保衛戰
- 央廣網濟南2月19日消息2月19日上午,山東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全面推進美麗山東建設,服務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的有關情況。山東...[詳細]
- 央廣網山東頻道 2025-02-19
威海鍛造過硬隊伍推動政法工作現代化
- 本報訊記者姜東良李娜通訊員宋建東山東省威海市委政法委連續四年以“狠抓落實”為主題,緊扣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通過...[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2-19
青島制定《辦法》加強地方標準管理
- 本報訊2月14日,山東省青島市政府新聞辦召開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青島市地方標準管理辦法》相關情況。根據上位法相關規定,界定市級地方...[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