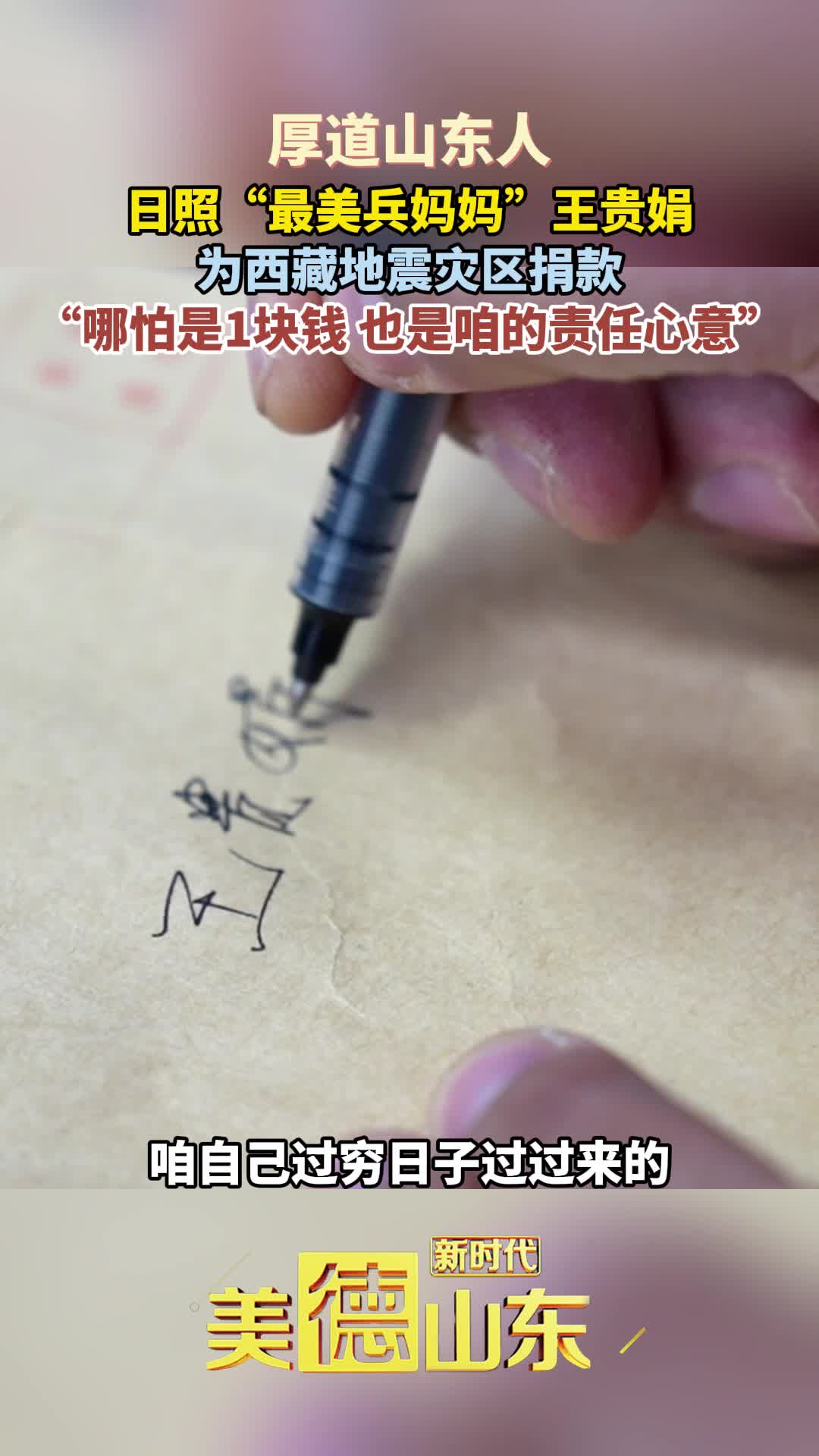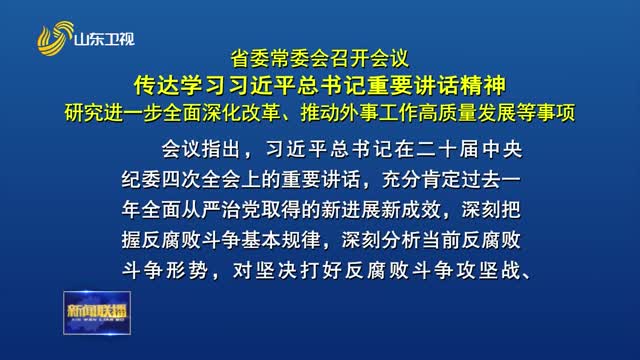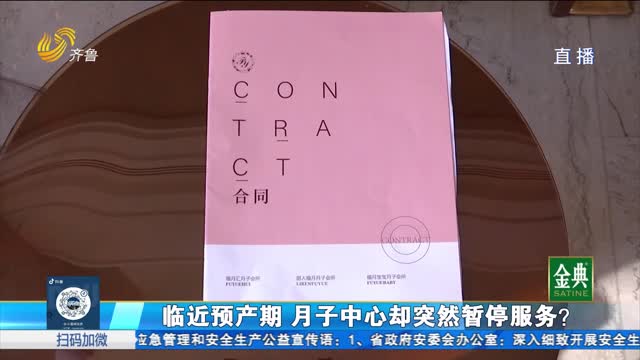靈蛇獻瑞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1-12 13:27:01
原標題:靈蛇獻瑞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靈蛇獻瑞
來源:光明日報
祥龍擺尾辭舊歲,金蛇狂舞鬧新春。每逢過年,民樂《金蛇狂舞》的激揚旋律便總是縈繞在大街小巷,烘托出熱烈喜慶的氣氛。這首樂曲由革命音樂家聶耳先生根據其故鄉昆明民樂改編而來,無論從音樂形象還是命名來看,都無不給人帶來力量與希望,充滿了畫面感。用聶耳自己的話說,他希望這首曲子“要讓聽的人都激動得跳起舞來”。
音樂家用抽象的音符,塑造出狂舞的金蛇,以不屈不撓、昂揚向上的精神,讓它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難忘記憶。回望歷史長河,國人描繪蛇的歷史頗為悠久。這些形態各異的蛇,不僅展現著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人的審美追求,更成為華夏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創造。
在中華民族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中,就可讀到有關蛇的詩句。例如《小雅·斯干》一篇里,便有“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之語,意指如果夢見蛇,那是將有女兒出生的吉兆。這既反映出蛇在古人心目中與女性之間的象征關系,更體現出其所蘊含的神秘屬性。
華夏民族很早就將蛇作為圖騰之一。建立了夏王朝的大禹,傳說其母名為“修己”,“己”與“巳”相通,而“巳”字的寫法又是從蛇形演化而來,所以“修己”的字面意思便是“修長的蛇”。一般認為,她便是來自以蛇為圖騰的部落。其子之名“禹”字的寫法其實也與蛇形有關。而大禹的兒子夏后啟,在《山海經》中亦被記載為頭飾兩條青蛇的形象。上古的神話傳說一再顯示出蛇在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這一點也為當今不少考古發現所印證。例如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其細長而扭曲的造型便應源于蛇的姿態。該器一端較大,左右對稱并呈方形布局,好似蛇的頭部,而其上兩個凸起的圓形裝飾,又與蛇眼十分相似。遍布器物全身的綠松石,以小塊拼鑲而成,一如蛇軀所覆鱗片那般閃亮。夏王朝這種源自蛇的圖騰信仰,對于后來逐漸融合而成的龍的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在“龍”字的繁體寫法中,依然保留著“巳”字的結構。
作為中華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圖騰,龍的形象廣為人知。然而,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考證的那樣,“龍”在最初本就是一種大蛇的名字,而龍具有蛇身,也能表明“龍的基調還是蛇”。國人至今都習慣將蛇稱為“小龍”,更將不少龍蛇形象的作品同題并論。山西陶寺的龍山文化遺址中曾出土一件距今4000年左右的“龍盤”。在這件新石器時代的著名遺物內側,以彩繪的方式描繪了一條卷曲的“蟠龍”。然而這條“龍”沒有足,其口部還繪有鋒利的牙齒與吐出的信子,這些正是蛇的特征。同時,先民們還用略帶弧度的筆觸,刻畫出遍布蛇身的鱗紋,進一步增強了畫面的寫實趣味。以蛇裝飾陶盤的做法,直到夏朝依然流行。現藏中國考古博物館的魚蛇紋大陶盆同樣出土于二里頭遺址,在其口沿的內側器壁上,堆塑了一圈蛇紋。這條蛇首尾相顧、纖細靈巧,同樣可被視為早期蛇崇拜的代表作。
上古先民對于蛇的崇拜,還集中體現在對神話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上。例如夸父、共工等,其造型都與蛇有關。夸父逐日的傳說十分有名,而據記載,他便是耳戴兩條黃蛇玉飾,左右兩手各執黃蛇與青蛇的形象。共工原本是堯帝的臣子,后來逐漸演變為上古帝王和部落首領,他則有著人首蛇身的外貌,且其臣屬兇神相柳亦是九首蛇神。在眾多與蛇有關的神仙形象中,尤以華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媧最為經典而知名。
由于保留了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存,至少在戰國時代,關于女媧的傳說已經廣泛流傳。屈原在他的《楚辭·天問》中,就曾發出“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的嘆問。東漢文學家王逸在此句下面注解道:“女媧,人頭蛇身。”指明了女媧的形象。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T形帛畫”頂部中央,便可看到人首蛇身的女媧畫像。這尊女媧像上半身為漢代女性造型,蛇軀則纏繞成團,凌駕于描繪墓主靈魂升仙場景的整幅畫面之上,顯示出其重要性。東漢時期,女媧信仰更為流行,其傳說故事也更為完備,她以造人與補天的不朽功勛,成為中華民族萬世敬仰的創世女神。
除了單獨出現,女媧與伏羲更常被一同描繪。東漢詩人王延壽曾經游覽過魯國境內的靈光殿。這座華美的建筑,始建于西漢景帝時期,幸免于兩漢之際的兵火,還保留有繁復的壁畫裝飾。游覽過后,王延壽寫下著名的《魯靈光殿賦》,文中歷數了他當時所寓目的畫面,“伏羲鱗身,女媧蛇軀”的圖畫赫然在列。盡管今天已經無法看到魯靈光殿壁畫中的伏羲女媧,但是從兩漢時期所保留下來的不少畫像石中,依然可以看到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形象。例如在山東沂南北寨以及嘉祥武氏祠等處出土的畫像石中,就時常可以看到繪有伏羲女媧的畫面。他們分別位于畫面的右側與左側,各自手中舉著曲尺與圓規,上半身朝向不同,但下半身纏繞在一起。刻工甚至還用波浪線刻畫出鱗片的痕跡,強調出蛇軀的質感。值得注意的是,蛇軀顯然并不僅限于伏羲女媧的表現,在二人周圍翻飛的羽人也被刻畫成人首蛇軀的模樣。因此,或許可以認為“人首蛇軀”正是兩漢之際仙人造型的特征之一,而這也顯示出蛇在此時所散發出的神性魅力。
流行于兩漢之際的伏羲女媧像,確立了這類圖像表現的基本模式,影響十分廣泛深遠。從中原到西南,從東部到西北,甚至在新疆,都能看到伏羲女媧像的遺存,其中又以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墓葬群集中出土的繪制于公元3至8世紀之間的大量伏羲女媧圖帛畫最為引人關注。雖然這些帛畫看上去構圖相似,但仔細觀察,卻不難發現伏羲、女媧的妝容和服飾亦隨時代變遷而變化。這些不盡相同的伏羲女媧像,不僅反映出各歷史時期的風貌,更是中華文明交融的生動寫照。
兩漢時期,除了將蛇軀與人首相結合,塑造出伏羲、女媧等諸多神仙形象外,還將蛇與其他動物組合在一起,形成更為豐富的神仙圖像譜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玄武形象的產生。至少在戰國時期,“玄武”就被確定為北方之神,后又因循五行學說成為水神。一直以來,“玄武”都是僅以龜為形,直到漢代才轉變為龜蛇相結合的圖案并流傳至今。在大量的漢代瓦當、畫像石中,都可以看到幾條蛇纏繞于龜身的玄武形象。東漢后期,隨著道教的興起,玄武又被吸收成為該教所崇奉的神明并越發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特別是在宋、明兩朝,對于玄武的信仰尤甚。千百年來,這龜蛇一體的形象始終默默守護著北方的安寧。
除了與龜結合,歷史上人們還將蛇與兔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達美好的祝愿。至今民間還流傳著“蛇盤兔,必定富”的說法。人們認為,當生肖兔與蛇的人結婚,必將大富大貴。這一說法的起源尚不清楚,但卻反映出民間對于美滿生活的向往。在陜西、山西等地區的民間剪紙中,一直保留著這一經典主題。這些剪紙造型生動,構思精巧,往往利用蛇的卷曲身姿,形象地將兔子“盤”起,一如玄武的形象那般,展現二者之間緊密的聯系,象征婚姻的美滿幸福。
民間剪紙中常見的蛇形象,除了“蛇盤兔”題材以外,還有“蛇神”。這類剪紙往往刻畫雌雄對偶的人首蛇身形象,與伏羲女媧圖像存在一定的聯系,但又已經擺脫了伏羲女媧的標志性特征,進而演化為純粹的蛇神。
中國民間最為家喻戶曉的“蛇神”,恐非《白蛇傳》中的白蛇、青蛇莫屬。這個古老的傳說,講述了千年白蛇化身報恩的故事,歷來為百姓津津樂道。其中諸如水漫金山、游湖借傘等不少經典場景更是被傳統剪紙與年畫廣為表現。以白蛇、青蛇為代表的所謂“義妖”,實際上正是反映人心冷暖的鏡鑒;而對于他們的喜愛,也恰好展現出廣大中國百姓崇尚正義與良善的品格。
從《金蛇狂舞》的飛揚曲調到蛇化為龍的圖騰變換,從伏羲女媧的人首蛇軀到龜蛇、兔蛇相融合的吉祥意涵,古往今來,蛇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中如影隨形、相生相伴。它承載了厚重歷史與美好祝愿,穿梭于人神之間,游弋在耳目心田,護佑著國泰民安。
(作者:王瑀,系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副研究員)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金石學史研究與刻帖書法新探
- 本報記者李亦奕以金石學史的方法感觸歷史金石學,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史考...[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5-01-12
以創作為核心探索畫院發展新路徑
- 云上220×220厘米2024年茹峰浙江畫院本報記者李百靈畫院是我國美術創作研究的重要力量,對于推動新時代文藝繁榮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日...[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5-01-12

天道酬勤鑄不凡——《經濟日報》聚焦青島港“人民工匠”許振超
- [詳細]
- 經濟日報 2025-01-12

《新華每日電訊》頭版聚焦?山東開年消費市場:場景提檔升級 活力持續釋放
- 山東省著力擴大內需,實施提振消費十大專項行動,今年開年以來,消費場景不斷提檔升級,消費活力持續釋放。[詳細]
- 新華每日電訊 2025-01-12

尋魯味 過大年丨“好品山東·魯采年貨節”在京開幕
- 人民網北京1月11日電雖然天氣寒冷,卻阻擋不住市民熱情的腳步,紛紛到北京魯采三元橋“趕大集”,感受年味。1月10日,備受市民關注的“采物...[詳細]
- 人民網山東頻道 2025-01-11
全國公安機關開展系列活動
- 本報北京1月10日電1月10日是第五個中國人民警察節。記者從公安部獲悉 10日,全國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開展了升警旗、唱警歌、重溫入警誓...[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1-11
老面饅頭“蒸”出鄉村新氣象
- 在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新區海青鎮甜河村共富茶食聯營工坊內,工作人員正在熱火朝天地制作傳統老面饅頭。該工坊通過批量化、標準化生產饅頭、...[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1-11
從“就近就便”轉向“就優就好”
- 近日,山東濰坊坊子區黃旗堡街道中心小學學生家長王成山告訴記者,他的孩子原本在黃旗堡街道逄王小學就讀。曾經的逄王小學,全校僅有19名平...[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1-11
用心維權解民憂 標本兼治提效能
- 投訴舉報是市場監管工作的“民意線”、市場秩序的“晴雨表”。嚴格落實山東省市場監管局投訴舉報24小時回應機制,認真執行“一口受理、依責...[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1-11
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 職業教育作為與地方產業聯系最為密切的教育類型,一直在青島城市建設和更新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來自教育一線的政協委員,青島市政協委員...[詳細]
- 人民政協報 2025-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