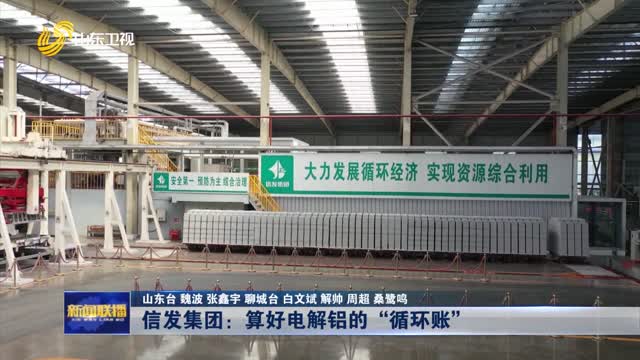山水間的往事
來源: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4-12-16 22:05:12
原標題:山水間的往事
來源:海報新聞
原標題:山水間的往事
來源:海報新聞
初春的夜晚,微風輕撫,已不似冬日的刺骨,如輕紗拂面,一股暖意涌上心頭。正值望月,皎潔的月亮懸于空中,抬眼望去,那山,那水若隱若現……立時,一幅山水之間的記憶浮現在眼前……
1973年的夏天,一輛綠色中巴車在山間的路上疾馳。出安陽城后,這輛綠色中巴就一直往西開。路越來越窄,樹越來越多,漸漸地,山出現了,慢慢的,山越來越高,再往前走,層巒疊嶂,山連了起來……
曾經,父親給我描述過太行山區的景致,小河,鮮花,各色各樣的鳥,漫山遍野的山果……
想著這些期待已久的景致,便總覺得車開得太慢,恨不能馬上到父親部隊駐地。
到部隊家屬區時,已是黃昏時分。
家屬區坐落在一個山坳里,四周都是黑黝黝的山,只是在山與山之間有幾個出口。在一個慢坡上,有一排一排的平房,我們住在最后一排俗稱屋山頭的最邊上的房子。房子是里外兩間。緊挨房子是一片荒涼的山坡,山坡上零星散落著幾座墳,墳頭上還有上墳人留下的白花。
當天晚上,刮起了風,風很大,一會兒像哨聲,一會兒又像有人在到處拍打。墳頭上的白花兒嘩啦嘩啦響,在漆黑的夜空中,只見一個個白條子飛來舞去。遠處,貓頭鷹的叫聲陣陣傳來,瘆的人渾身起雞皮疙瘩。我和二弟嚇得鉆到床里邊,一動不敢動。
直到半夜,才迷迷糊糊睡去。突然,父親的叫聲又將我們驚醒:“醒醒,醒醒……別站起來,慢慢下床。”
站到床下,我們驚訝的望著父親,不知發生了什么事。這時,父親才指了指蚊帳里面,我一看,一只蝎子正晃著尾巴趴在蚊帳的上面。父親將蝎子打死,才轉身說:“這東西尾巴上有毒,蜇上一下,那可不得了……好了,沒事兒了,睡吧。”
可哪還睡得著呀!
山里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剛到那幾天,白天沒事,就到處瘋跑。與夜晚不同,陽光下的山色很美,藍藍的天,綠綠的山,清香撲鼻的空氣,悅耳的鳥鳴,到處綠樹蔥蔥。有松樹、柏樹、柿子樹、核桃樹、山楂樹等,路邊,多是長得不高的酸棗樹和花椒樹。我們采了許多的花椒,回家去了外皮,把里邊的花椒籽炒著吃,不僅不麻辣,還很香。
最令我奇異的是山上的溪水,水很清澈,也很淺,可就這淺淺的溪水里竟然也游著小魚。
山上鳥兒很多,許多都叫不上名字,最多的是麻雀,成群結隊,飛來飛去。逮鳥兒,就成了我們一個樂此不疲的活動。食堂的戰士有午休的習慣,我們就趁他們午休的時候,把食堂盛饅頭的大簸籮偷偷地拿來逮鳥。簸籮很大,直徑足有一米多,我們把大簸籮倒扣在山坡上,用一根小棍支起來,下面撒些小米,小棍兒上拴根繩,手里抓著繩的另一端藏起來,不一會兒,傻傻的麻雀就會飛到簸籮下吃小米,這時,一拉繩,麻雀就被扣到了簸籮下。
為了不影響我們的學業,父親送我們到附近的村子里去上學。這是一所合辦小學,學生主要是部隊和附近村里的孩子。學校很簡陋,教室是磚瓦房,泥土地面,坑洼不平,黑板是刷黑了的泥墻。同位兒共坐一張長條凳,共用一張木質長桌,沒有桌洞。
山里的孩子普遍能干,也能吃苦,學校條件雖然簡陋,可是那些農村孩子學習卻很認真。我的同位兒就是個很認真的女孩。她上課從不說話,書總是整整齊齊放在桌子一角。她還在桌子中間劃了一條線,不讓越線,她也從不越線。她喜歡管人,還喜歡向老師告狀。
因為這里的學習進度比北京慢,老師講得我都會,于是,上課時就不好好聽了。同位見我總搞小動作,就一次次地找老師告狀。挨了老師的批評后,我便決定報復她一下。
一次,她站起來回答問題,回答完往下坐的時候,我一下站了起來,長條凳翻了,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這下,老師生氣了,把我叫到辦公室,狠狠地批了一頓。
老師說:“回去把你媽叫來。”
我一聽到媽媽兩字,眼睛濕潤了,眼淚在眼眶里直打轉。老師見狀,沒再追究,說了我幾句就讓我回去上課了。
晚上,父親問我,老師讓叫你媽,你哭什么?
我說,我想媽媽了!
這是我長到十來歲第一次離開媽媽!
雖然在這個山村小學時間不長,但和很多同學都成了好朋友。
其中,有個女孩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一個秀氣的女孩,圓臉,微黑的臉上,一雙大大的眼睛,黑眼球特別大,烏黑的頭發,梳著兩個大辮子,雖然衣服上打了好幾個補丁,可是非常干凈,合體。她學習一般,但她非常愛看書。每次課間,她總有許多問題要問。她從沒離開過這個小山村,可是對山外的向往卻無時無刻不在她的大眼睛里閃現。知道我從北京來,她問得最多的就是北京。北京,在她的眼里是非常遙遠,又很神圣的地方。
有時,她也給我講一些山里的事情,尤其是說起山里的好吃的,眼里總是放著光,說得津津有味兒,每次都說得我要流口水。我在想,山里竟有這么多的好東西,她真有口福。
一天,她一到學校,就從藍布書包里拿出一個黑黑的窩頭,問我“吃嗎?”
我一見,很是高興,我太喜歡吃地瓜面窩窩頭了,喜歡那粘粘的、甜甜的味道。她見我喜歡,抿嘴笑了。
“我知道你們北京城里的人吃不到這個,你們多是吃細糧。”
說著話,一個地瓜面窩窩頭就進了我的肚里,吃完,我還意猶未盡,說道:“明天再給我帶一個來唄。”
“嗯。”她爽快地答應了。
第二天,她沒有帶來。我問她,她告訴我,媽媽沒蒸。又過了幾天,她還沒帶來,又問她,她說,跟媽媽說過了,可是媽媽還是沒蒸。
“那你們這些天都吃的什么?”
“玉米餅子,地瓜面窩頭平時很少吃。”她回答。
因為不服山區的水土,我開始鬧肚子,肚子整天脹得鼓鼓的,父親決定提前送我們回去。
上完在這個山村小學的最后一節課,我興高采烈地離開教室,終于要回北京了,終于要回家了,終于可以吃上媽媽做的香噴噴的飯了。邊想著,邊往外走,剛出校門,聽到后邊有人叫我,轉過身,是她,兩個眼睛黑亮黑亮的,俊俏的臉通紅,額頭上還有細微的汗珠。她從藍色的布書包里拿出了兩個黑黑的地瓜面窩頭。
“我剛回家拿來的。”喘了喘,她輕輕地說。
接過窩窩頭,還是熱的……
時光荏苒,一晃,30多年過去了。雖歷經歲月磨礪,可是,童年的記憶卻越發清晰。山里人的質樸、善良至今難以忘卻,就像那溪水一樣清澈,就像那山色一樣秀美。(作者張代生 文章寫于2014年)
[ 責編:李伯璽 ]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第九屆全國道德模范候選人公示!山東這些人入選!
- 為充分發揮道德模范榜樣引領作用,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立精神支柱、樹價值標桿、育時代新人,中央宣傳部、全國總工會、共青...[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4-12-16
第三屆濟南國際雙年展開幕
- 12月15日,第三屆濟南國際雙年展在山東美術館和濟南市美術館開展,此次雙年展匯聚了來自21個國家和地區的215位藝術家,共展出291件作品。展...[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4-12-16
第三屆稷下國家治理高端論壇在山東大學舉辦
- 12月14日-15日,由山東大學主辦、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和山東大學智庫建設中心承辦的第三屆稷下國家治理高端論壇于山東大學中心校區舉行...[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4-12-16
河口區全力做好鹽堿地特色農業文章 加強綜合利用 打造后備糧倉
- 愛東營訊日前,在河口區六合街道五號水庫旁,麥田泛著淡淡的綠色。”張學文所在的地塊,屬于五號水庫南片區和廟二片區鹽堿地綜合利用試點項...[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4-12-16
將支付改革融入醫院管理格局
- □山東省濰坊市高密市人民醫院郭其貞王俊杰高密市醫療保障局魯勇自2020年開始,山東省濰坊市實行按病種分值付費支付,2023年起落實月度預結...[詳細]
- 健康報 2024-12-16
嚴查酒駕醉駕背后風腐問題
- 本報訊近期,山東省青島市平度市公職人員李某醉酒后駕駛機動車,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查獲。該線索被移交給平度市紀委監委后,紀檢監察機...[詳細]
-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4-12-16
昌樂“月通報、季晾曬”督促治水
- 本報記者董若義通訊員魏翠玉濰坊報道“成立59支‘共建美麗幸福河湖’志愿服務隊,設置13個志愿服務站;縣環委會牽頭有關部門,逐步形成興水...[詳細]
- 中國環境報 2024-12-16
山東嚴打重型柴油貨車污控裝置弄虛作假
- ◆周雁凌季英德王艷迪在位于山東省棗莊市市中區的十里泉停車場內,停放著數十輛重型柴油貨車。山東省機動車排氣污染監控中心、棗莊市生態環...[詳細]
- 中國環境報 2024-12-16

《求是》刊發山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白玉剛署名文章:做好文化賦能 譜寫齊魯華章
- [詳細]
- 求是 2024-12-16
山東對臺交流基地講解員大賽舉辦
- 本報棗莊12月15日電山東對臺交流基地講解員大賽近日在棗莊市臺兒莊區舉辦,參賽選手及評委、山東各地市臺辦有關負責同志等共100余人參加活...[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4-12-16
推進高校協同創新 履行服務社會責任
- 陳甜甜趙鳳娟《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以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為核心,以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為主線,加快一流...[詳細]
- 中國文化報 2024-12-16
檢查后請醫生看報告單,該推門進還是排隊等?
- 閱讀提示二次報到的門如何“推開”,困擾著一些患者,同時,也對醫院管理提出了更細化的要求。眼看其他患者一個個按號進入診室,他只能在門...[詳細]
- 工人日報 202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