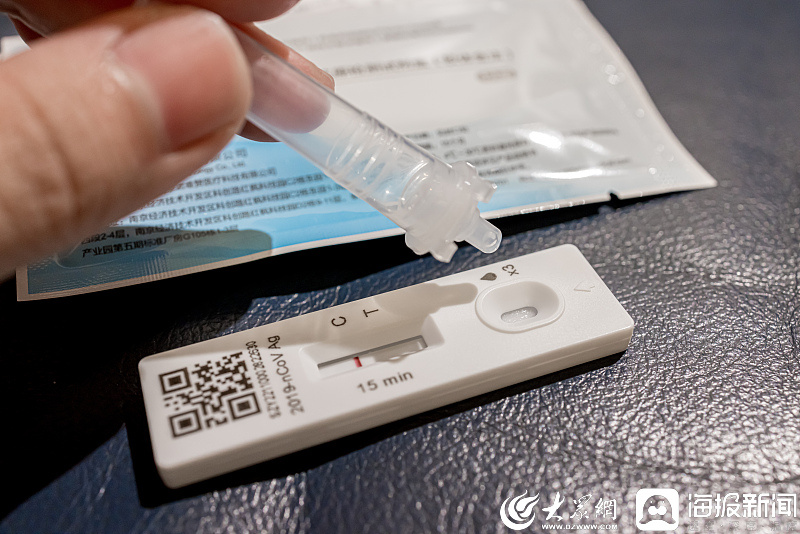尋河探運(yùn)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2022-12-30 10:29:12
原標(biāo)題:尋河探運(yùn)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原標(biāo)題:尋河探運(yùn)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尋河探運(yùn)
京杭大運(yùn)河百年來首次全線通水 中華“命運(yùn)之河”的歷史記憶也在疏通
( 2022-12-30 ) 稿件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年終報(bào)道
本報(bào)記者劉夢(mèng)妮、張典標(biāo)
冬日暖陽下,北京通州西海子公園的燃燈塔佇立在藍(lán)天下。風(fēng)吹過,塔身飛檐懸掛的風(fēng)鈴開始搖曳,不時(shí)發(fā)出悅耳的叮鈴聲。
過去,南來的跑船人經(jīng)歷數(shù)月艱辛,一看見燃燈塔心里就踏實(shí)了。這是京杭大運(yùn)河的北方終點(diǎn)。
2022年4月,全長約1794公里的京杭大運(yùn)河,終于迎來100多年來首次全線通水。人們不禁暢想從北京到杭州泛舟觀光的場景,也會(huì)帶著懷古幽思走進(jìn)大運(yùn)河的歷史,從這條承載家國興衰的“命運(yùn)之河”中理解中國。
早在通水前,對(duì)于這條南北大動(dòng)脈,考古工作者梁紀(jì)想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勘探過,攝影家劉世昭一個(gè)鏡頭一個(gè)鏡頭記錄過,作家徐則臣一步一字地考察書寫過。
對(duì)他們來說,今年同樣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梁紀(jì)想投入到通水清淤時(shí)挖出的沉船研究;劉世昭將自己跨越35年兩次騎行大運(yùn)河時(shí)拍下的珍貴照片捐贈(zèng)首都博物館;徐則臣仍在繼續(xù)著他的運(yùn)河文化探索與推廣。在他們眼里,這條世界上開鑿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運(yùn)河,不僅是人類偉大水利工程的歷史見證,更承載著文化、歷史、經(jīng)濟(jì)……滋養(yǎng)著運(yùn)河兩岸。
一個(gè)“運(yùn)河考古人”的“執(zhí)念”
在滄州文旅局文物保護(hù)中心副研究員梁紀(jì)想看來,通水保護(hù)了文物。“大運(yùn)河斷流的時(shí)候,好多人在運(yùn)河邊挖掘當(dāng)年沉船留下的銅錢、瓷器。現(xiàn)在通水了,這種現(xiàn)象也消失了。”
早在2004年,梁紀(jì)想就和同事踏上了京杭大運(yùn)河滄州段的調(diào)查之路。
歷史上的滄州因運(yùn)河而興。“長河日暮亂煙浮,紅葉蕭蕭兩岸秋。夜半不知行遠(yuǎn)近,一船明月過滄州。”清代孫諤的《夜過滄州》,為人們勾勒出當(dāng)年京杭大運(yùn)河滄州段通航的美景勝境。
而當(dāng)梁紀(jì)想他們開啟調(diào)查時(shí),京杭大運(yùn)河滄州段已斷流多年,“干涸的河道里長出了草,還有人在河里放羊。”
調(diào)查中,梁紀(jì)想見到了很多耄耋之年的老人,都盼著運(yùn)河能再次通水,“老百姓對(duì)運(yùn)河很有感情,還口口相傳著當(dāng)年運(yùn)河纖夫的故事。”
從滄州青縣與天津交界的九宣閘開始,梁紀(jì)想和六七個(gè)同事分成兩個(gè)小組,沿著運(yùn)河兩岸徒步走到滄州吳橋。
他們帶著GPS、尺子、手鏟、背包、相機(jī)等工具,白天做田野調(diào)查,晚上整理資料,200多公里的京杭大運(yùn)河滄州段,他們走了一個(gè)多月。歷史上這段運(yùn)河彎多水急,這次調(diào)查的重點(diǎn)是那些不幸葬身運(yùn)河的沉船。
“我們主要是探訪運(yùn)河兩岸的村子,調(diào)查村里老人所了解到的運(yùn)河沉船情況,包括沉船的位置、大概的年代,這些信息都是一代代口口相傳下來的。”梁紀(jì)想說,去年年初,京杭大運(yùn)河滄州段清淤時(shí),在泊頭挖出了一艘沉船,地點(diǎn)跟當(dāng)年了解到的基本一致。
一個(gè)多月里,梁紀(jì)想和同事們記錄下20多個(gè)沉船點(diǎn)。其中,大多數(shù)沒有歷史記載。
運(yùn)河兩岸廢棄的磚窯,也讓梁紀(jì)想印象深刻。“這些磚窯離運(yùn)河特別近,主要是方便運(yùn)輸。”梁紀(jì)想解釋,“燒制的磚專供北京城墻、宮殿和廟宇。每塊磚差不多五六十斤重,上面還刻著年號(hào)。”
當(dāng)時(shí),村里好多老房子、圍墻包括豬圈,都是用這些廢棄的磚修建的。梁紀(jì)想他們收集了一些磚,送到省博物館保存。
調(diào)查結(jié)束后,梁紀(jì)想輾轉(zhuǎn)河北多地進(jìn)行考古勘探,但一直沒有離開運(yùn)河。他曾在河北省大運(yùn)河申遺辦公室工作,親歷了京杭大運(yùn)河申遺成功的喜悅。
隨著京杭大運(yùn)河全線通水,滄州再次享受到運(yùn)河水的滋潤。
梁紀(jì)想的家離運(yùn)河大約一公里,他晚飯后常常去運(yùn)河邊散步,“這一帶現(xiàn)在漂亮多了,走在運(yùn)河邊,跟過去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作為考古工作者,他希望所有的沉船一直安靜地留在河底,“這其實(shí)是一種保護(hù)”。因此,他們當(dāng)年調(diào)查出那些沉船點(diǎn)后,一直沒有開挖。
泊頭河道發(fā)現(xiàn)沉船后,他們趕到現(xiàn)場看到,部分沉船被挖土機(jī)挖出,已經(jīng)能看見船板了。“我們先用水沖刷船上的淤泥,然后估量船體長寬,再在周圍打木樁,把船整體吊出來。”
他們?cè)谏舷掠渭俺链c(diǎn)附近都打了壩攔水,但大運(yùn)河里有很多泉眼仍在冒水,導(dǎo)致沉船點(diǎn)附近的壩老是垮。梁紀(jì)想親自下河,參加挖掘和修建河壩,“在泥里干活,我穿著雨鞋雨褲,還是一身水、一身泥。”
2021年,在滄州段南川樓建筑工地上,又發(fā)現(xiàn)兩艘金元時(shí)期的木質(zhì)沉船。沉船附近及船體上出土了銅錢、瓷器及其碎片。梁紀(jì)想說,金在北京設(shè)金中都,隨后元朝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遙想當(dāng)年,南來北往的貨船,在滄州的運(yùn)河上絡(luò)繹不絕。
目前,梁紀(jì)想和同事們正投入南川樓沉船發(fā)掘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除了拍照、錄像、繪圖、做標(biāo)簽、文字描述,他們還將沉船浸入純凈水水池中,讓堿和鹽從沉船中排出。他解釋說,滄州鹽堿地特別厲害,所以要對(duì)沉船進(jìn)行排鹽排堿處理。
神奇的是,經(jīng)過排鹽排堿處理的沉船,外觀基本沒有變化,“可見當(dāng)年做船用的都是好木頭。”梁紀(jì)想說。
一個(gè)“運(yùn)河攝影師”的“騎拍史”
劉世昭也見識(shí)過滄州鹽堿地的厲害。
1981年,這位《人民中國》雜志攝影記者第一次騎行京杭大運(yùn)河時(shí),吃得最咸的地方就是滄州。
劉世昭記得,一小盤青椒炒肉絲,一頓吃不完。因?yàn)槌灾滩艘粯印T跍嬷萜悴瑁愕迷贊獠杷蚕獭?5年后劉世昭再去,“就沒這事兒了,菜不那么咸了,而且各種口味都有。”
兩次騎行,劉世昭見證了運(yùn)河沿岸和人們生活的變化。1981年,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搞不懂什么叫改革開放。2016年,運(yùn)河沿岸人們的生活因改革開放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1981年6月,33歲的劉世昭和文字記者沈興一起,從北京出發(fā)沿著京杭大運(yùn)河騎行,一邊騎一邊在沿岸的城市、村莊采訪。
他們避開了盛夏最熱和寒冬最冷的時(shí)間段,將行程分為4個(gè)部分,歷時(shí)400多天,在1983年1月到達(dá)杭州。
第一次騎行時(shí)還是用膠片拍攝,劉世昭舍不得隨便拍。但整個(gè)行程也拍攝了3000多張膠片,記錄下了改革開放初期京杭大運(yùn)河沿岸的風(fēng)土人情。
2016年春,已經(jīng)退休的劉世昭,再次騎行京杭大運(yùn)河。他直接從北京騎到杭州,歷時(shí)68天,拍了718G照片,按每張照片10MB計(jì)算,粗略估計(jì)有七八萬張。
兩次騎行,劉世昭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個(gè)“變”字。這讓他欣喜,也讓他惆悵。
他向記者展示的京杭大運(yùn)河照片中,有張第一次騎行時(shí)在常州簸箕巷拍攝的。充滿古典氣息的江南水鄉(xiāng),沿岸民居與運(yùn)河、舟楫、古橋融為一體。
第二次騎行到達(dá)常州后,他興致勃勃地想舊地重游,卻幾乎迷了路。
這次拍的照片中,運(yùn)河拓寬了,古橋不見了,兩岸的民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綠地,完全沒了過去的影子。
劉世昭指著第二張照片連連搖頭,“單看這張,你會(huì)覺得這城市挺好。有居民樓、寫字樓,綠化也好,但是跟過去一對(duì)比就忍不住想問,怎么弄成這樣了?”
那些消失的古香古色,讓劉世昭悵然若失。山東聊城大運(yùn)河畔的山陜會(huì)館,是京杭大運(yùn)河漕運(yùn)的見證。第一次騎行路過這里時(shí),劉世昭特意起了個(gè)大早。當(dāng)時(shí)運(yùn)河干涸,幾只綿羊在山陜會(huì)館前的河床上吃草。他舉起相機(jī),把這份獨(dú)特的蒼涼之美定格下來。
多年后,他再次來到這里,改變最大的就是山陜會(huì)館前的大運(yùn)河:寬闊的河面、清澈的河水、石砌的堤岸、整齊的欄桿……為運(yùn)河通水而開心的劉世昭,心中依然有種失落,感覺眼前的景色修飾得太新了。
在天津,他最惦記的是當(dāng)年吃過的大油餅。油餅直徑70厘米,重量估計(jì)在1斤以上,一口鍋只能炸一個(gè)。
這種大油餅是漕運(yùn)時(shí)代的遺存,運(yùn)河上的裝卸工、纖夫勞動(dòng)強(qiáng)度大,又沒錢吃大魚大肉,就選擇這樣的大油餅來填飽肚子。
劉世昭拍下了攤主金寶成炸大油餅的場景,又買了一個(gè)和同事分而食之,兩個(gè)大男人就都吃飽了。
35年后,劉世昭在河西務(wù)幾經(jīng)打聽才找到油餅攤子,可惜老金已經(jīng)不在了,是他遠(yuǎn)房親戚家的孩子在經(jīng)營。油餅炸得薄了,吃法也不一樣,會(huì)根據(jù)顧客的口味添加作料及羊雜碎,比過去好吃很多。
“時(shí)代在變,人們的飲食習(xí)慣也在變,現(xiàn)在誰還會(huì)一口氣吃一斤的大油餅啊,”劉世昭感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大油餅的消失是理所當(dāng)然的。”
在蘇州運(yùn)河上的船艙里,劉世昭的鏡頭記錄了一個(gè)三四歲的小男孩,被繩子拴在船上玩耍。這是1980年代初跑船人的生活。為了安全,船家常把孩子拴在船上。
如今,船家都上岸安了家,這樣的情景再也看不到了。
在兩岸風(fēng)物的變遷中,古老的大運(yùn)河見證了中國的變化,中國的變化也改變了大運(yùn)河及其沿岸。
“看到了,拍到了,記錄下來,就覺得沒白跑。”74歲的劉世昭,這樣形容自己跨越35年的兩次京杭大運(yùn)河騎行。
第二次騎行結(jié)束沒多久,劉世昭體檢查出癌癥。“如果晚一年,估計(jì)騎行就干不成了。”他感慨地說。
好在他恢復(fù)得不錯(cuò),現(xiàn)在出門也愛騎車,天氣好的話每天都要騎上10公里。
今年,劉世昭將自己兩次騎行大運(yùn)河時(shí)拍下的照片全部捐贈(zèng)首都博物館。記者上門采訪時(shí),他正在整理膠卷,桌上堆著幾十盒膠卷盒子。“作為攝影人,我要把見到的盡量記錄、保存下來,因?yàn)檫@就是運(yùn)河的歷史。”
一個(gè)“運(yùn)河作家”的“運(yùn)河觀”
梁紀(jì)想挖掘的運(yùn)河沉船,也被作家徐則臣寫進(jìn)了小說《北上》。這本2019年獲得茅盾文學(xué)獎(jiǎng)的小說,開篇就是一份京杭大運(yùn)河沉船考古報(bào)告的摘錄。
徐則臣寫了20多年大運(yùn)河。大運(yùn)河通水前,他在接受采訪時(shí)感嘆,“大運(yùn)河已經(jīng)死掉了一半,濟(jì)寧以北早已斷流,很多河道已經(jīng)湮滅。”
如今全線通水,他認(rèn)為也不能代表大運(yùn)河的再生——通水只是物理意義上活了,更重要的是挖掘大運(yùn)河文化和精神上的內(nèi)涵,真正“喚醒”大運(yùn)河。
其實(shí),徐則臣對(duì)大運(yùn)河的認(rèn)識(shí),也經(jīng)歷了從物理意義到精神意義的轉(zhuǎn)變。
徐則臣的故鄉(xiāng)在江蘇東海。小時(shí)候,學(xué)校門口就有一條運(yùn)河。夏天在河里游泳、打水仗;冬天自來水管被凍住,大家拿著牙刷、端著臉盆在河邊洗漱。“我從小跟水的關(guān)系就很親密,那時(shí)河流對(duì)我來說,只是有用而已。”
18歲在江蘇淮安上大學(xué)時(shí),徐則臣第一次見到京杭大運(yùn)河。“從我們校門往南步行10分鐘,就是運(yùn)河。一些跟京杭大運(yùn)河有關(guān)系的古跡,比如清江閘、清江浦,就是我們?nèi)粘I畹囊徊糠帧!?/p>
多年以后,當(dāng)徐則臣開始寫作時(shí),自然而然地寫起了運(yùn)河。但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他來說,寫運(yùn)河跟寫別的河沒有區(qū)別,“運(yùn)河只是故事的背景。”
直到2014年,京杭大運(yùn)河申遺成功。徐則臣和出版社朋友聊天時(shí)撞擊出火花,決定寫一部關(guān)于京杭大運(yùn)河的長篇小說,讓運(yùn)河故事由背景走向前臺(tái)。
接下來的4年里,徐則臣做了大量田野調(diào)查和案頭工作。市面上關(guān)于京杭大運(yùn)河的書,能找到的他基本都看了。劉世昭的《流淌的史詩——京杭大運(yùn)河騎行記》,他也翻閱過。
徐則臣還一次次從工作地北京出發(fā),把運(yùn)河沿線重要城市和水利樞紐走了個(gè)遍。他遇見很多在運(yùn)河邊畫畫和拍攝的人。在《北上》小說里,他創(chuàng)作了孫宴臨這個(gè)人物。小說中孫宴臨潛心研究過郎靜山的攝影作品,而郎靜山的家鄉(xiāng)就在淮安。歷史的真實(shí)和小說虛構(gòu)就這樣交織在一起。 大多數(shù)時(shí)間里,徐則臣漫無目的地走走看看,河水的流向、流速、清澈度,河道彎曲程度,岸邊的莊稼、植物、建筑、游玩的人……他都感興趣。他也不知道這些細(xì)節(jié)在寫作中會(huì)不會(huì)用上,但就這樣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有一次,徐則臣去德州出差,想順便到運(yùn)河邊看一看,卻找不到河道。他問路邊躺椅上乘涼的老大爺運(yùn)河在哪。順著大爺手指的方向,徐則臣一看,那不是一條路嗎?上面已經(jīng)長滿了荒草。
老大爺說,他小時(shí)候還經(jīng)常在那玩水,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路了。
這件事讓徐則臣有一種滄海桑田之感。“千年的大河最后成了路。我們過去對(duì)運(yùn)河的保護(hù)的確不夠,或者說我們沒意識(shí)到運(yùn)河的重要性,現(xiàn)在好多了,各地都很關(guān)注運(yùn)河。”
“它不僅僅是一條河,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線索和脈絡(lu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徐則臣發(fā)現(xiàn)京杭大運(yùn)河功能性意義之外,還承載著中華文明與悠久歷史。
徐則臣認(rèn)為,隋唐以后,中國大一統(tǒng)趨勢(shì)之所以越來越強(qiáng),是因?yàn)榫┖即筮\(yùn)河把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5大水系聯(lián)通起來,打破過去南北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上的隔絕,實(shí)現(xiàn)了連接與交流。
除此之外,中國文化跟水有密切關(guān)系,水流的方式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
“這些觀點(diǎn)都是我琢磨出來的,不知道專家會(huì)怎么看。”徐則臣說,“但顯而易見,沒有這條河,中國歷史會(huì)是另一番樣子。”
創(chuàng)作《北上》時(shí),徐則臣曾寫過運(yùn)河流經(jīng)徐州,但審稿專家指出,那一年京杭大運(yùn)河變道,沒流經(jīng)那里。于是他把那一大段故事全部刪掉了。
他告訴記者:“如果純粹寫一條想象中的運(yùn)河,我可以隨便寫,但我希望能寫出一條真實(shí)的運(yùn)河,那么這種硬傷是不能有的。”
徐則臣剛開始寫運(yùn)河時(shí),關(guān)注京杭大運(yùn)河的人并不多。“那時(shí)我覺得這無關(guān)緊要,后來寫《北上》,發(fā)現(xiàn)了京杭大運(yùn)河的重要,就希望別人也能關(guān)注它。”
在徐則臣看來,京杭大運(yùn)河全線通水是推廣運(yùn)河文化的契機(jī)。“有了眼前這條活生生的運(yùn)河,我們就更有機(jī)會(huì)看到它的歷史文化價(jià)值。即使暫時(shí)看不到,只要運(yùn)河一直在流,不斷觸動(dòng)我們,早晚會(huì)讓我們產(chǎn)生探究的愿望。”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司法責(zé)任制度建設(shè)的探索
-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責(zé)任制改革深入推進(jìn),有力促進(jìn)了司法為民、司法公正。回溯人民法院司法責(zé)任制度建設(shè)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始自新民主主義革...[詳細(xì)]
- 人民法院報(bào) 2022-12-30
“碼上舉報(bào)” 讓監(jiān)督更便捷
- “‘碼上舉報(bào)’幫我們解決了問題,辦證沒有人敢吃拿卡要。“碼上舉報(bào)”是紀(jì)檢監(jiān)察機(jī)關(guān)利用信息技術(shù)手段建立的貼近群眾的便捷舉報(bào)渠道。“碼...[詳細(xì)]
- 人民法院報(bào) 2022-12-30
以替人消災(zāi)為名誘騙老年人錢財(cái)
- 4個(gè)騙子冒充醫(yī)生、病人和指路人,以替人消災(zāi)為名騙人錢財(cái),兩名老年人被騙去現(xiàn)金25020元和價(jià)值657元的銀手鐲。石某、李某、趙某、魏某均是...[詳細(xì)]
- 人民法院報(bào) 2022-12-30
開展孝善幫扶 保障脫貧戶生活
- 本報(bào)訊(通訊員孟慶峰李娜)“現(xiàn)在吃穿方面不用愁,今年閨女給我們老兩口交了孝善金,加上財(cái)政補(bǔ)貼一共5280元,這讓我們老兩口心里熱乎乎的...[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2-12-30
藍(lán)領(lǐng)群體就業(yè)呈現(xiàn)新趨勢(shì)
- 制造業(yè)藍(lán)領(lǐng)投遞簡歷的數(shù)量是服務(wù)業(yè)的3倍多,勞動(dòng)密集型制造業(yè)始終是藍(lán)領(lǐng)就業(yè)主力軍;求職群體主要來源于人口大省、用工集中省份和人口流出...[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2-12-30
小村“噶蛹者”開啟節(jié)日之“戰(zhàn)”
- 閱讀提示隨著元旦、春節(jié)臨近,作為東北團(tuán)圓家宴一道“硬菜”的蠶蛹開始熱銷。在如火如荼的產(chǎn)業(yè)鏈背后,一群來自小村的95后、00后年輕人,成...[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2-12-30
以系統(tǒng)觀念謀劃人工濕地建設(shè)
- ◆徐立文近年來,恢復(fù)和建設(shè)人工濕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得到了地方的廣泛重視。以山東省為例,經(jīng)過多年建設(shè)和修復(fù),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覆蓋全省主要排污...[詳細(xì)]
- 中國環(huán)境報(bào) 2022-12-30
齊魯大地綠水青山將統(tǒng)一“定價(jià)”
- 本報(bào)訊為推動(dòng)山東省生態(tài)產(chǎn)品價(jià)值核算工作,確保核算的科學(xué)性、規(guī)范性和可操作性,山東省生態(tài)環(huán)境廳日前發(fā)布全省首個(gè)《山東省生態(tài)產(chǎn)品總值(...[詳細(xì)]
- 中國環(huán)境報(bào) 2022-12-30
用好生態(tài)環(huán)保財(cái)政資金
- ◆張厚美近日,財(cái)政部下達(dá)了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多項(xiàng)2023年生態(tài)環(huán)保資金預(yù)算,預(yù)算總額達(dá)到2089億元。在需求收縮、供...[詳細(xì)]
- 中國環(huán)境報(bào) 2022-12-30
2021年度金牛董秘獎(jiǎng)
- 勝華新材呂俊奇科沃斯馬建軍廣匯能源倪娟中糧科技潘喜春智飛生物秦菲伊利股份邱向敏甬金股份申素貞昊華科技蘇靜祎生益科技唐芙云新日股份王...[詳細(xì)]
- 中國證券報(bào) 2022-12-30
山東青島:構(gòu)建金融科技能力 助力普惠金融發(fā)展
- 實(shí)體經(jīng)濟(jì)也一直是青島的立市之本、強(qiáng)市之基。2019年12月,在青島市地方金融監(jiān)督管理局、青島市大數(shù)據(jù)局指導(dǎo)下,由青島國信集團(tuán)攜手浪潮集團(tuán)...[詳細(xì)]
- 中國日?qǐng)?bào)網(wǎng) 2022-12-30
“好聲音”唱響“主旋律” 青島市即墨區(qū)打造“即宣即講”理論微宣講品牌
- 那么,請(qǐng)您靜下心來,我們一起去追尋為了今天的美好而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革命印記,其中,即墨巾幗英雄崔淑蘭的英勇事跡,就是我們要用一生來...[詳細(xì)]
- 中國日?qǐng)?bào)網(wǎng) 2022-12-30
回到常識(shí)閱讀文學(xué)經(jīng)典
- 溫儒敏老師有多重身份,而這些身份可以對(duì)應(yīng)大致三個(gè)場域的工作 文學(xué)研究、文學(xué)教育和文學(xué)生活。《溫儒敏講現(xiàn)代文學(xué)名篇》一書恰是將三種場...[詳細(xì)]
- 中國教育報(bào) 2022-12-30
- 12022卡塔爾世界杯決賽頒獎(jiǎng)典禮 梅西捧起大力神杯
- 2林冠夫:蕭齋寂寂一燈紅
- 3緊急提醒:“陽了”之后,這件事千萬別做
- 4《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點(diǎn)贊山東重點(diǎn)藥企科學(xué)排產(chǎn)穩(wěn)定預(yù)期 全力保障群眾用藥需求
- 5鐘南山:99%感染者可在7至10天內(nèi)完全恢復(fù)
- 6《經(jīng)濟(jì)日?qǐng)?bào)》刊文點(diǎn)贊中國重汽——破局而立 向新而生
- 7《光明日?qǐng)?bào)》訪山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白玉剛:深耕齊魯人文沃土 推進(jìn)文化自信自強(qiá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