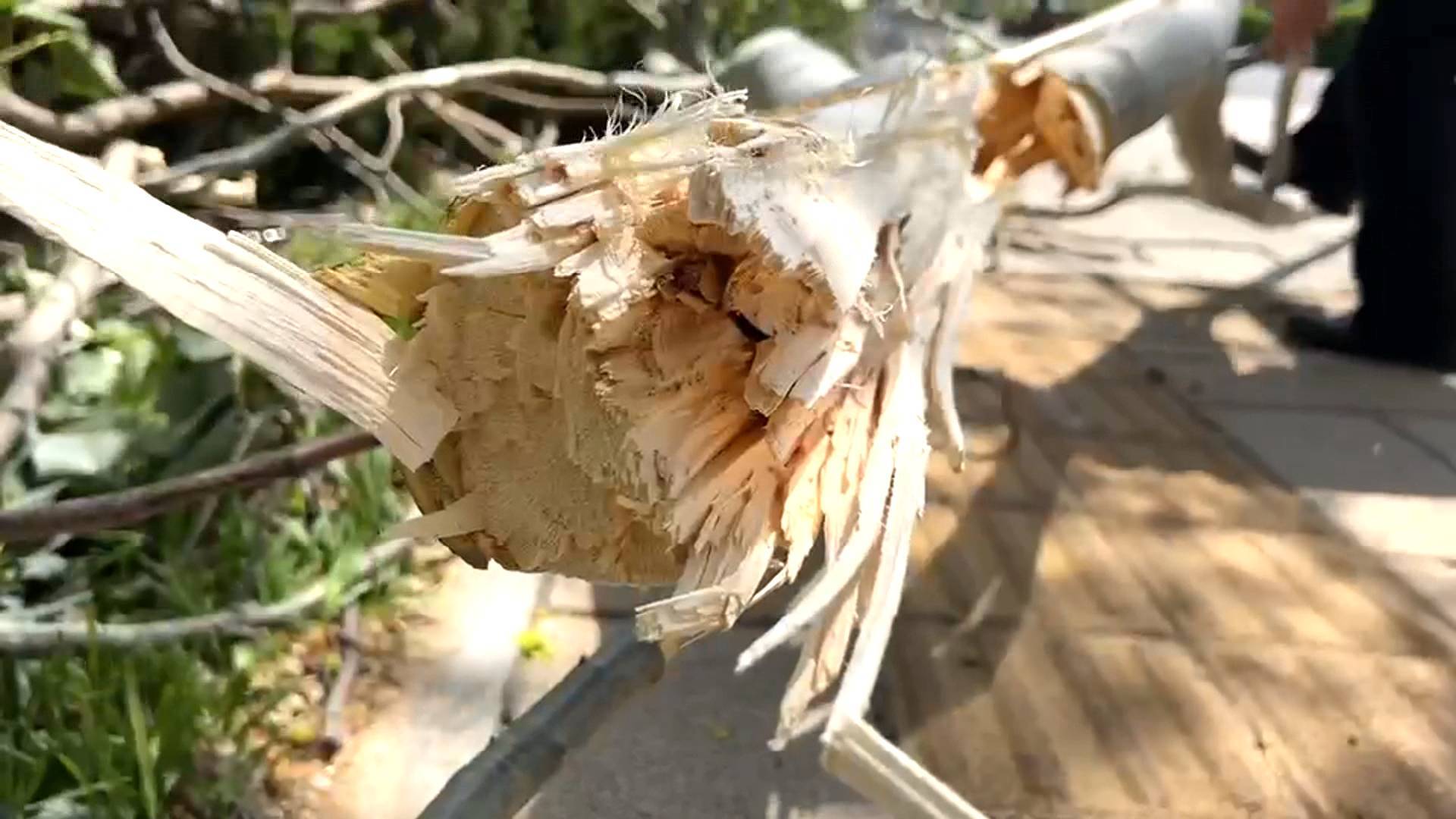散文如何寫開頭
來源:解放軍報
2025-04-13 14:06:04
原標題:散文如何寫開頭
來源:解放軍報
原標題:散文如何寫開頭
來源:解放軍報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寫散文亦如此。縱觀名家散文的開頭,寫法各有千秋,但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先聲奪人”。理想散文的開頭,猶如運用中國水墨畫的“潑墨法”,將蘸著情感的筆墨潑灑在文字里,既有瞬間定格時空的巧思,又暗藏貫穿全篇的氣韻。
且看沈從文《湘行散記·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的開頭:“我仿佛被一個極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個聲音還在耳朵邊。原來我的小船已開行了許久,這時節正在一個長潭中順風滑行,河水從船舷輕輕擦過,把我弄醒了。”這里的“先聲奪人”在于用水聲喚醒了記憶,而且還像“極熟”的人喊的。這就巧妙地抒發了作家對家鄉山水的情感,也描述了虛實交織的敘事場景,讓讀者領略到由聽覺漣漪擴散出的、帶有溫度的湘西山水長卷。
朱自清的《背影》是人們熟知的名篇,開頭看似平淡,卻讓人印象深刻:“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這種開篇點題的寫法,將抽象的情感化為具體的意象“背影”。文中提到兩年的“不相見”,更像是畫家的“留白”,為讀者提供了想象空間和讀下去的懸念。這種借物理距離丈量心理距離的開頭,就很容易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散文開頭的形式應是多變的,絕非只有某幾種固定模式,這才是名家寫作的真功夫。名家名篇的開頭,無論以何種面目出現,都可用寥寥數語,牢牢抓住讀者眼球。老舍《濟南的冬天》開頭,引入了一個虛擬的對話:“對于一個在北平住慣的人,像我,冬天要是不刮風,便覺得是奇跡;濟南的冬天是沒有風聲的。”這虛擬的對話者“你”,通篇也沒有出現,卻時時感覺就在作家和讀者的身旁。這于無形中,讓作家和讀者之間就會產生了親近感。開篇的對話切入,遠比平白的敘述,要靈活得多、風趣得多。老舍一開頭便將“北平”和“濟南”的冬天加以類比,反襯出濟南這座古城的“溫暖”與“深情”,整篇散文充滿詩情畫意,也表現出他對濟南的熱愛與懷念。
初學寫作者往往糾結于開頭如何寫,如何吸引人,即便搜腸刮肚,用了美麗的辭藻,可寫得還是平平,這就是因為尚不懂得寫散文開頭的要領。其實,寫開頭大可不必挖空心思去杜撰不切實際的語言,名家散文的開頭往往很簡潔。像魯迅的《秋夜》,“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但放在秋夜里來寫,卻是意味深長的。看似是一種文字的重復,卻暗含著作家孤寂凝視中的情感成分。汪曾祺《端午的鴨蛋》開頭就更簡潔了:“家鄉的端午,很多風俗和外地一樣。”這種白描的筆法,只是一種鋪墊,先“同”后“異”,為后文的鴨蛋驚艷“亮相”埋下了伏筆。這類開頭可以使散文在平淡中見奇崛。
寫到這兒,我不禁想到余光中寫雨的名篇《聽聽那冷雨》。這篇散文的開頭:“驚蟄一過,春寒加劇。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天潮潮地濕濕,即連在夢里,也似乎把傘撐著。”這段文字寫得很美,但美的不只是散文語言,更是美在內心深處。從字面上,作家用了料峭、淋漓、淅瀝3組疊字,透過疊字的渲染,可以領略到初春的“冷雨”與他的思鄉心緒是息息相通的。當年余光中走在“冷雨”中,走在春寒料峭的臺北,滴滴冷雨打在他的傘上,也打在他的心里。一句“即連在夢里,也似乎把傘撐著”,可謂點睛之筆,讓我聯想到他的那首著名詩作《鄉愁》:“……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一個好的開頭就像散文寫作路口的路標。路標指向對了,往往就會寫得很順,反之就處處別扭,甚至無法順暢地寫下去。同一篇散文,同一個人也可以試寫幾個不同的開頭,這就猶如有諸多路口,總有一個路口是最適合自己的。我們不妨以名家為師,找到適合自己的那個路口,向著散文寫作的最佳路徑出發吧。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好客山東·齊魯1號”旅游列車投入運營
- 光明日報濟南4月12日電煥然一新的K8281次列車4月10日從濟南站駛出,標志著“好客山東·齊魯1號”旅游列車正式投入運營。“好客山東·齊魯1...[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5-04-13
高鐵寵物托運服務正式啟動
- 本報訊4月10日,高鐵寵物托運服務正式啟動。第一批“毛孩子”在全國多個試點車站登上列車,同主人一起趕赴目的地。中鐵快運明確,高鐵寵物...[詳細]
- 中國青年報 2025-04-13
山東當前水土保持率達86.55%
- ??日前,記者從山東省水土保持工作會議上了解到,當前,山東省水土保持率達到86.5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3.72個百分點,全省連續多年水土...[詳細]
- 新華網山東頻道 2025-04-13
山東:今年力爭數字經濟占GDP比重超50%
- ??日前,山東數字強省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數字強省建設2025年工作要點》,聚焦加力釋放數據要素價值、加力培育數字經濟發展新動能、...[詳細]
- 新華網山東頻道 2025-04-13
首屆山東綠色蔬菜產業博覽會在山東蘭陵開幕
- 4月12日,首屆山東綠色蔬菜產業博覽會在山東蘭陵縣啟幕。上海市五角興農城同步舉辦了沂蒙優質農產品走進上海·蘭陵推介活動,并與開幕式現...[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5-04-12
做好檢察管理促高質效辦案落細落實
- “三個管理”的核心目標是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其中業務管理側重宏觀管理,質量管理側重結果管理,而案件管理則是對個案處置流程進行管理...[詳細]
- 檢察日報 2025-04-12
9城市納入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
- 新華社北京4月11日電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的批復11日發布。根據方案,在已有試點地區基礎上,將大連市、...[詳細]
-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25-04-12
山東955場次女性專場招聘助6萬余名女性就業
- 中國婦女報全媒體記者姚建發自濟南近日,記者從山東省婦聯獲悉,為深入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于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決策部署,落實省委、省政府...[詳細]
- 中國婦女報 2025-04-12
應急管理部對十三個省份啟動強對流天氣預警響應
- 本報北京4月11日電記者從中央氣象臺獲悉 氣象監測顯示,4月11日白天,北方出現大范圍大風沙塵天氣,新疆南部、內蒙古、甘肅、青海北部和東...[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4-12
青島國際郵輪母港單日客流破萬創紀錄
- 4月10日,首艘國產大型郵輪“愛達·魔都號”圓滿結束韓國濟州-日本福岡5天4夜的航行,靠泊青島國際郵輪母港,在青島邊檢站移民管理警察的...[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5-04-11
六百余專家齊聚青島!探索飯店業發展新引擎
- 在數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當下,飯店業正經歷變革與重塑,創新成為行業破局的強引擎。4月9日至11日,山東省旅游飯店協會第五屆第五次會員大會...[詳細]
- 中國日報網 2025-04-11
山東濰坊:民營企業跳動在時代脈搏中的前行者
- 2024山東民營企業百強系列榜單中,濰坊31家企業入選2024年山東民營企業200強,13家企業入選2024年山東民營企業創新100強,16家企業入選2024...[詳細]
- 央廣網山東頻道 2025-04-11
黃河流域“9+3”知識產權高質量發展聯盟年會在豫舉辦
- 本報訊4月8日,黃河流域“9+3”省知識產權高質量發展聯盟年會在河南省焦作市舉辦,與會單位共商知識產權轉化運用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大計。...[詳細]
- 中國市場監管報 2025-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