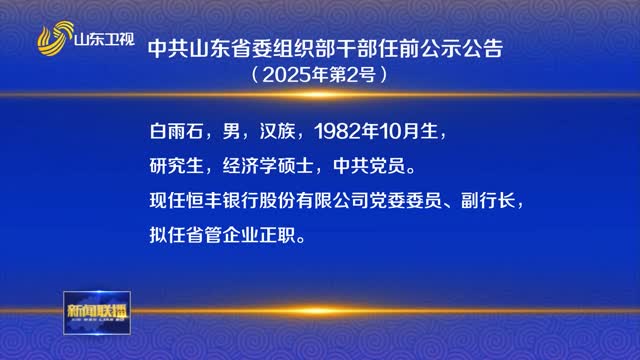海上明月共潮生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3-24 08:57:03
原標題:海上明月共潮生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海上明月共潮生
來源:光明日報
袁行霈在賞析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一詩時指出:“第二句‘海上明月共潮生’,告訴我們那一輪明月乃是伴隨著海潮一同生長的。詩人在這里不用升起的‘升’字,而用生長的‘生’字,一字之別,另有一番意味。明月共潮升,不過是平時習見的景色,比較平淡。明月共潮生,就滲入詩人主觀的想象,仿佛明月和潮水都具有生命,她們像一對姊妹,共同生長,共同嬉戲。這個‘生’字使整個詩句變活了。”(袁行霈《如夢似幻的夜曲——〈春江花月夜〉賞析》)與此類似,張靜在賞析張九齡《望月懷遠》一詩時指出:“為什么‘海上生明月’用的是‘生長’的‘生’而不是‘升起’的‘升’?‘升起’的‘升’只表現了位置的由低到高的上升,而‘生長’的‘生’是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還可以與次聯的‘起’產生呼應。”(葉嘉瑩等講讀《唐詩三百首:名師抖音共讀版》)今人對古詩中“生”“升”之辨的關注程度,可見一斑;而相關說法尤其常見于中學語文詩歌鑒賞類著述,有意引導學生將之視為“煉字”的典范,從想象、擬人等修辭角度來分析這兩個字的區別。
其實,古詩中寫月而用“生”字的,不可勝數,如陳子昂“微月生西海”(《感遇》其一)、李白“揚帆海月生”(《荊門浮舟望蜀江》)、韋應物“片月生幽林”(《懷素友子西》)、李賀“涼月生秋浦”(《蜀國弦》)等皆是,以至于俗文學敦煌曲子《楊柳枝》里也有“月生月盡月還新”(《老催人》)這樣的表達。據劉延玲統計,《全唐詩》中“月生”有67條之多,而“月升”僅3條。當然不僅是唐人才如此遣詞,南北朝庾信有“月生無有桂”(《鏡詩》),宋代張先有“莫放修蘆礙月生”(《題西溪無相院》),元代王冕有“今夜初生月”(《十二月三日對月》),明代屈大均有“不知山月生”(《攝山秋夕作》),清代袁枚有“拄杖忽驚新月生”(《客里》),可謂已成熟套。
當然,古詩不僅是寫月,寫其他無生命之物,也常用到“生”字。比如“云”,李白有“云生結海樓”(《渡荊門送別》),杜甫有“蕩胸生層云”(《望岳》),杜牧有“白云生處有人家”(《山行》)。又如煙,王昌齡有“寒煙生里閭”(《客廣陵》),李白有“日照香爐生紫煙”(《望廬山瀑布》),李商隱有“藍田日暖玉生煙”(《錦瑟》)。可見“生”字在古詩中的使用范圍是很廣的。
而且值得注意,古詩中“生”“落”二字可以成對出現。如宋代耿镃有“月生月落洞庭波”(《西樓》),元末明初李昱有“青山缺處殘日落,碧海盡頭明月生”(《晚興》),明末清初王夫之有“月落月生春易改”(《春月歌》),清代蔣士銓有“日落月生時”(《瀟湘靜·薛壽魚屬題云華校書圖》),均以“生”“落”連用。“生”既與“落”連用成對,其主要含義也就與“升”并無太大差別。按照我們現在的邏輯,“升”“落”應該是一對,用于描述簡單機械的空間變化;“生”“死”應該是一對,用于描述生命歷程的狀態。兩對詞組在詞義、意境等方面區別顯然,斷不能混淆等同。然而這些詩句偏不說“日死月生”或“日落月升”,而要以“生”“落”連用相對,這就無可辯駁地證明今日通行的邏輯和解讀與古詩的真實情形并不相符。
還有一個現象也可證明這種古今差異:與今人對“生”字的津津樂道形成鮮明而有趣的對照,古人評點幾乎不談“生”字的問題。比如張若虛的“海上明月共潮生”,康熙《御選唐詩》卷九注云:“《抱樸子》:‘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大。’楊泉《物理論》:‘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海嶠志》:‘潮隨月虧盈。’”其闡釋方向不是“月”與“生”的關系,而是“月”與“潮”何以“共”生的關系。又如張九齡《望月懷遠》,明代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稱道其“‘滅燭’‘光滿’四字,已盡月之神”,清代屈復《唐詩成法》卷一稱道其“‘共’字逗起‘情人’,‘怨’字逗起相思”,卻無人稱道其“生”字用得妙。王灣《次北固山下》頸聯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引徐充的話,倒是提及了“生”字,不過說的卻是:“‘生’字、‘入’字淡而化,非淺淺可到。”也就是說,徐充所稱道的不是“生”字的使用很特別,而是很平淡,平淡到宛若天成,這當然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化境。所以明代李攀龍《唐詩訓解》也說這兩句是“淡而難求”。
由此可見,寫無生命之物而用“生”字,古人已是慣見熟聞,習而相忘。在他們眼中,“生”字簡直平淡無奇,因此不會予以特別表揚,更不會又拈出一個“升”字作為假想敵來推敲取舍一番。
實際上,這種習而相忘的情形,提示著我們關注古人的固有觀念。錢鍾書指出,“以死物看作活”,“無生者如人忽有生”,譬如杜甫之“四更山吐月”、王安石之“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這樣的句子“開卷即是”,多不勝數。(錢鍾書《談藝錄》)究其原因,則如錢先生后來所說:“蓋吾人觀物,有二結習:一、以無生者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錢鍾書《管錐編》)當然,嚴格區分出“有生”“無生”,也是以今人觀念來闡說古人,而古人觀念應如方東美所說是“萬物有生論”:“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現象里邊都藏著生命。”(方東美《中國人生哲學》)在古人看來,萬物皆是“有生”,皆是陰陽變化的結果。《周易·系辭上》云“生生之謂易”,王弼注云“陰陽轉易,以成化生”,《系辭下》又云“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揭示了陰陽與化生之關系。《系辭上》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勾勒了萬物從無到有、由簡而繁的化生圖景。《系辭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孔穎達疏云“言天地之盛德,在乎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指明了萬物化生不息的永恒性特征。孔子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也是這種化生觀念的體現。
這種化生觀念產生兩個結果:一是萬物一體,二是我們今日認為的無生命之物,在古人那里,天然具備生命特征。就第一個結果而言,劉延玲對“生”“升”的辨析是恰當的:“面對‘大海’‘明月’同一情景,‘升’所關聯兩個物體之間的關系,是外在的,冷漠的,無情的。‘生’所連接的兩個事物,則有一種緊密的聯系,是內在的,溫暖的,有情的。”(劉延玲《海上明月之“生”與“升”——兼及古典詩詞里的“字”文化與“情”哲學》)就第二個結果而言,我們就會發現,用“想象”“擬人”等修辭手法來解讀“生”字,其實并未真正讀懂這個“生”字。因為在古人那里,“生”是對萬物實然狀態的說明,并非通過“想象”而“擬”人。
《芥子園畫傳》直接稱呼石頭為“云根”,認為云就像植物一樣是有生機、會生長的,而且還有“根”——這絕不是什么“想象”“擬人”,而是他們的固有觀念。傳統山水畫中這樣的例證還不少。不過在這個問題上,“鑒畫衡文,道一以貫”(錢鍾書語),更加體現出化生觀念已如空氣一樣充分籠罩著古人,所以他們寫月、云、煙等無生命之物而選用“生”字,不足為奇。那么,在解詩時向讀者講古人固有的觀念,比起講今人推測的修辭,似乎更有價值。
(作者:李寶山,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公募REITs進入常態化發行新階段
- ●本報記者昝秀麗南方順豐物流REIT公眾投資者發售部分3月21日提前結募;匯添富上海地產租賃住房REIT公眾投資者發售部分3月17日提前結募;南...[詳細]
- 中國證券報 2025-03-24
農技人員入田指導小麥春管
- 連日來,山東省聊城市茌平區積極開展2025年“萬人下鄉·穩糧保供”農技服務行動,組織全區150余名農技人員,深入田間地頭指導農民科學進行...[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3-24
聚焦重點作物 做好技術培訓
- 近日,由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中國農藥工業協會、中國農藥發展與應用協會主辦的2025年全國百萬農民科學安全用藥培訓啟動儀式在山東省...[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3-24
2025年山東省首屆南繁成果展示觀摩現場會舉行
- 本報訊近日,山東省農業農村廳種子管理總站在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黃流鎮南繁科研育種基地舉行2025年山東省首屆南繁成果展示觀摩現場會,集...[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3-24
我國發現首個億噸級頁巖油田
- 光明日報記者宋喜群、馮帆通訊員徐永國、賈玉濤記者22日從中國石化勝利油田獲悉,我國油氣勘探領域迎來重大突破——中國石化勝利油田濟陽頁...[詳細]
- 光明網山東頻道 2025-03-24
全力破案攻堅 上門便民利企
- □本報記者林珊通訊員石亞男近日,山東省威海市乳山公安機關經縝密研判、周密部署,成功偵破系列保險詐騙案,抓獲犯罪嫌疑人6名,涉案金額3...[詳細]
- 人民公安報 2025-03-24
走,到田間海邊上課去!
- 近日,山東省濱州市沾化區濱海鎮實驗學校六年級學生王嘉怡說。據介紹,濱海鎮實驗學校邀請鹽業企業專家進行技術指導,在學校建立了“小鹽場...[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24
思政教育融入環境和生活
- 近年來,山東濰坊高新區浞景學校堅持以美養德、以美育人,把美育、德育與學校生活深度融合,讓學生在活動中得到浸潤和發展,蹚出了一條別具...[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24
課堂筆記的為何與何為
- 課堂筆記作為一種傳統學習方式,對于學生學習的意義是什么。回答好這兩個問題,對于廣大一線教師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教學價值。做好課堂筆...[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24
流行歌曲與中考作文的“夢幻聯動”
- ■有些流行歌曲的歌詞與中考作文的核心主題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學生在優美旋律中,不知不覺積累了好詞好句■在考試現場寫命題作文,流行歌曲...[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24
解鎖花田里的“基因密碼”
- ◎本報記者俞慧友春日的長沙,油菜花田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3月21日,記者來到農業農村部湖南油菜綜合科研試驗基地,湖南農業大學教授劉忠...[詳細]
- 科技日報 2025-03-24
易過敏人群如何過好春天
- 易過敏人群如何過好春天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健康新華社南寧3月22日電打噴嚏、流鼻涕、眼睛癢、皮膚紅腫……春季是過敏高發季節,易過敏人...[詳細]
- 新華每日電訊 2025-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