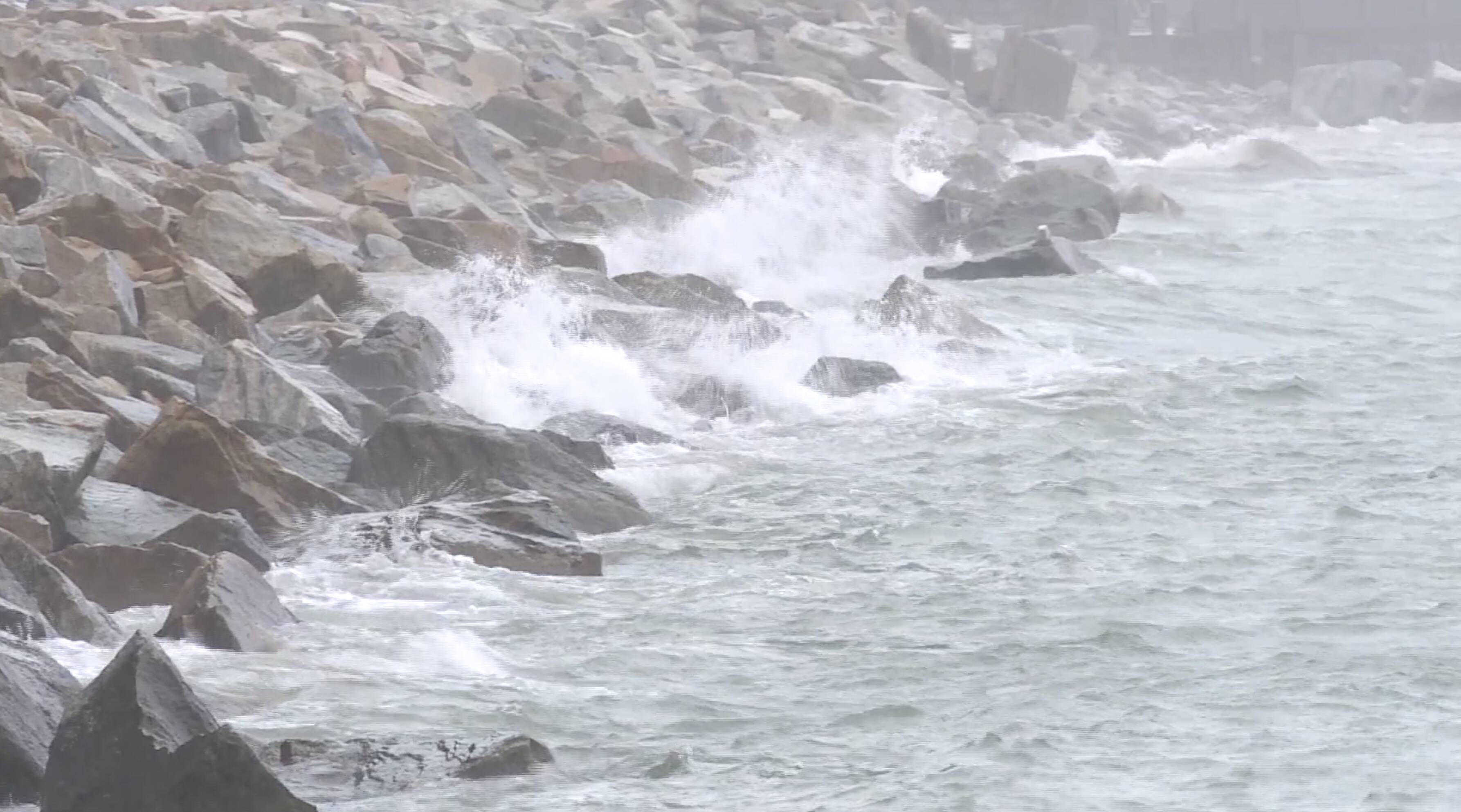問刑典范:晚明呂坤《刑戒》法文化解析
來源:人民法院報(bào)
2022-09-30 09:04:09
原標(biāo)題:?jiǎn)栃痰浞叮和砻鲄卫ぁ缎探洹贩ㄎ幕馕?/p>
來源:人民法院報(bào)
原標(biāo)題:?jiǎn)栃痰浞叮和砻鲄卫ぁ缎探洹贩ㄎ幕馕?/p>
來源:人民法院報(bào)
呂坤(1536—1618年),字叔簡(jiǎn),晚明河南歸德府寧陵(今河南商丘寧陵縣)人。萬歷二年(1574年)中進(jìn)士,初為山西襄垣知縣,因政績(jī)卓著,于萬歷三年(1575年)調(diào)任大同。萬歷十二年(1584年)后,任吏部主事。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任刑部右侍郎,旋轉(zhuǎn)左。在任期間,包括以《刑戒》為代表的問刑方案在內(nèi),呂坤的治世建議代表了當(dāng)時(shí)士大夫群體對(duì)于國政頹廢的積極應(yīng)對(duì)態(tài)度。(以下所引呂坤之內(nèi)容參見《呂坤全集》,王國軒、王秀梅整理,中華書局2008版)
《刑戒》的內(nèi)容要點(diǎn)與問世原因
面對(duì)明代中后期司法領(lǐng)域的嚴(yán)重弊端,身在刑曹的呂坤強(qiáng)烈呼吁“居官所慎,民命為先。民命所關(guān),獄情為重”,《刑戒》當(dāng)是因時(shí)而作,共八類32條,主要針對(duì)刑訊泛濫但又不得不刑訊問案的實(shí)際而制。正如呂坤所言:“紀(jì)綱法度整齊嚴(yán)密,政教號(hào)令委曲周詳,原是實(shí)踐躬行,期于有實(shí)用,得實(shí)力。今也自貪暴者奸法,昏惰者廢法,延及今日,萬事虛文。甚者迷制作之本意而不知,遂欲并其文而去之。”于是,刑訊的技術(shù)直接簡(jiǎn)化為“暫時(shí)不打”和“始終不打”兩個(gè)大類。“暫時(shí)不打”進(jìn)一步細(xì)分為“莫輕打”“勿就打”“且緩打”“莫又打”四類;“始終不打”則進(jìn)一步細(xì)分為“(絕)不打”“憐不打”“該打不打”“禁打”四類。從行刑者“我者”來看,有“且緩打”“莫又打”“憐不打”“禁打”四類,從受刑者“他者”的視角觀之,有“(絕)不打”“莫輕打”“勿就打”“該打不打”四類。八類32條又可任意組合,幾乎涵蓋了刑訊所涉的各種情形,且用朗朗上口、易于記誦的表達(dá)形式,傳教于官民,以期收到治理良效。
呂坤提出的“居官五要”之前兩要指出“休錯(cuò)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gè)人”,《刑戒》便是具體行動(dòng)方案,時(shí)任刑部尚書的蕭大亨與呂坤關(guān)系甚密,故而能助推其整頓問刑亂象。《刑戒》可謂以呂坤為代表的刑部規(guī)范刑訊的特別立法。呂坤認(rèn)為:“法之立也,體其必至之情,寬以自生之路,而后繩其逾分之私,則上有直色而下無心言。”《刑戒》即是秉持著這一立法宗旨而設(shè),32條的主要入選標(biāo)準(zhǔn)是是否關(guān)乎人倫、人法、人命和人案。但凡有違禮儀教化、有違律法規(guī)范、與受刑人性命攸關(guān)、有礙案件審斷的皆不可輕易用刑。人倫方面主要有尊長與卑幼訟不打。在禮法合一的時(shí)代,有違人倫和人法時(shí)有重合,主要包括:老、幼、病不打;宗室、官員、生員、婦人莫輕打。有違律法的主要是禁止性規(guī)范,包括重杖、從下(腿部以下)、佐貳非刑(官吏私自用刑)禁打,此三種情形也可能關(guān)乎受刑人性命。凡與性命攸關(guān)者需萬分謹(jǐn)慎,主要包括: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人急、人忿、人醉、人隨行遠(yuǎn)路、人跑來喘息勿就打;已拶、已夾、要枷莫又打;盛寒炎暑、佳節(jié)令晨、人方傷心憐不打。有礙公正斷案的主要包括:我怒、我醉、我病、我見不真、我不能處分且緩打;百姓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為修私衙或及買辦自用物不打。最后只剩下“上司差人莫輕打”,以防得罪上司,此條亦可歸為有礙司法(執(zhí)法)公正之列。總之,《刑戒》在于“戒昏”,為的是正大光明地刑訊斷案,以服人心,誠如他在《憂危疏》中所言:“刑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
《刑戒》32條是呂坤一直踐行的實(shí)學(xué)思想之體現(xiàn)。當(dāng)時(shí)空疏遷腐之風(fēng)盛行,呂坤卻強(qiáng)調(diào)事功和實(shí)政,令人別開生面,(馬濤:《論呂坤理學(xué)思想的特點(diǎn)》,《史學(xué)月刊》1989年第2期)以《刑戒》嚴(yán)厲要求官員“不敢刑、不能刑、不想刑”,讓官員能夠恰如其分地問刑辦案,把握分寸地積極履職,正是呂坤實(shí)政思想之核心“明職”與“定分”的展現(xiàn)。《刑戒》并非憑空而出,是呂坤為官一如既往地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和言行一致之累積。明末清初大儒李二曲曾在《四書反身錄》評(píng)價(jià)呂坤:“躬親講勸……視縣事若家事,視民產(chǎn)若己產(chǎn)。率作興事,不憚勞瘁。自作縣守府以至分巡濟(jì)南,布政陜右,巡撫山西,所在皆然。”為官一任,呂坤都要講“實(shí)用”:“天下萬事萬物,皆要求個(gè)實(shí)用。……是故明君治天下,必先盡革靡文而嚴(yán)誅淫巧。”在自撰的墓志銘中,呂坤將“非日用不談,非切民生國計(jì)不講”作為言行標(biāo)準(zhǔn),對(duì)可操作性技術(shù)和實(shí)務(wù)性細(xì)節(jié)一直相當(dāng)重視。例如在任山西按察使期間,他制定的《按察事宜》將自己的職權(quán)范圍和工作要點(diǎn)條分縷析,還自撰《安民實(shí)務(wù)》等手冊(cè)指導(dǎo)下級(jí)官員處理政務(wù),且多是從具體而微的技術(shù)指南出發(fā)踐行其實(shí)用主義的為政主張。(陳寒鳴:《呂坤啟蒙儒學(xué)散論》,載《儒藏論壇》2019年第1期)加之,呂坤認(rèn)為官吏普遍缺乏處理政務(wù)的必要知識(shí)是導(dǎo)致官場(chǎng)腐敗的重要原因,〔解揚(yáng):《期成實(shí)務(wù)的困難——呂坤〈實(shí)政錄〉在地方上的施行問題》,載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明史研究論叢(第九輯)》,紫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刑訊技巧的缺乏亦包括在內(nèi)。于是,呂坤在恰當(dāng)?shù)臅r(shí)機(jī)推出了《刑戒》以供同僚參鑒。
《刑戒》的適用傳播與時(shí)代影響
時(shí)值內(nèi)憂外患,奸臣當(dāng)?shù)溃諌嫞愘x苛重,“民心如實(shí)炮,捻一點(diǎn)而烈焰震天;國勢(shì)如潰瓜,手一動(dòng)而流液滿地矣。”在《刑戒》問世不久的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呂坤上奏《憂危疏》,言辭懇切地向萬歷皇帝直陳天下安危,指出要想挽救危局、延長國脈,“惟有‘固結(jié)人心’四字”。律法上則建議依律例辦事,減少詔獄,不要在真相沒有查清之前對(duì)宗室、勛戚、群臣、宮人以及百姓用刑,否則法令不嚴(yán)、用刑不一,造成過多的冤假錯(cuò)案,致民心盡失。這自然是對(duì)《刑戒》精神和部分內(nèi)容的重申。《刑戒》對(duì)下在前,《憂危疏》對(duì)上在后,呂坤希望君臣一體,同心同德,慎刑恤刑。然奏疏未能上報(bào),且遭給事中戴士衡誣告,呂坤憤然稱病乞休。
解揚(yáng)的研究指出,呂坤并非因上《憂危疏》得不到皇帝的反饋而乞歸致仕。堅(jiān)持實(shí)用主義的呂坤一直都努力與萬歷皇帝保持了當(dāng)時(shí)少見且較為融洽的君臣關(guān)系,這是包括《刑戒》在內(nèi)的實(shí)用主義建議能夠得到推行的關(guān)鍵保障,也是當(dāng)時(shí)身在廟堂的士大夫最想拯救萬民于水火的理想之法。當(dāng)時(shí)黨爭(zhēng)已起,呂坤尚不能置之事外,他自撰的《墓志銘》曾言:“在都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君堅(jiān)守一說,屹屹不為動(dòng)。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為危。君一稟天日,不懲始念。”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標(biāo)志著東林黨的形成。當(dāng)時(shí)吏部已完全擺脫了內(nèi)閣的控制,不愿內(nèi)閣干預(yù)考察之事。主察者是吏部尚書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當(dāng)年五月,呂坤升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正四品),因職位卑微,并未參與此次京察。到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四月吏部左侍郎員缺,呂坤成為京察對(duì)象,獲得會(huì)推但被詔另用。問題出在時(shí)任右都御史的沈思孝和內(nèi)閣大學(xué)士張位,與呂坤和吏部尚書孫丕揚(yáng)處在對(duì)立的政治陣營中。萬歷皇帝對(duì)牽涉黨爭(zhēng)的大臣十分厭惡,呂坤無意中觸犯了政治禁忌。時(shí)又恰逢震驚朝野的“董范之議”案,此案又與黨爭(zhēng)有關(guān),呂坤仍上書直抒己見,指責(zé)天威過重,懇乞明正法律,以服公論。而后的“朝鮮之議”則是在他上呈《憂危疏》的十二天前案發(fā),呂坤與因此被奪職的兵部尚書石星等人都有舊誼,他們?cè)诨实垩壑薪詫儆谀軇?wù)實(shí)理事而不務(wù)空言的黨派。呂坤頓感置身其中難以有所作為,遂決意求去避險(xiǎn)。(解揚(yáng):《萬歷封貢之?dāng)∨c君臣關(guān)系的惡化》,載《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因牽涉黨爭(zhēng),《刑戒》問世之后或未能得到地方官的足夠重視。
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由呂坤的門生、湖廣監(jiān)察御史趙文炳匯集校刻的《實(shí)政錄》面世,將呂坤之實(shí)用政治主張和為官技術(shù)操作和盤托出,惠及后人。《實(shí)政錄》卷六《風(fēng)憲約》所含“提刑事宜”52款,為呂坤出任山西等處提刑按察使時(shí)所頒告示,約成書于萬歷十八年(1590年),主要是針對(duì)“民生未奠”的六類事項(xiàng)“追呼苦于太濫、問斷苦于太淹、擬罪苦于太密、追贖苦于太刻、拘禁苦于太易、隸卒苦于太縱”,這些無不與刑訊相關(guān)。其中包括“監(jiān)禁十款、聽訟十二款、用刑四款”,成為《刑戒》的經(jīng)驗(yàn)依據(jù),再次印證了《刑戒》并非無源之水。
《刑戒》是否作為正式公文而發(fā)放全國不得而知,但在官場(chǎng)卻不脛而走,成為明末清初問刑的不二法門。《刑戒》能在明末清初產(chǎn)生廣泛影響正是得益于《實(shí)政錄》的盛名。2013年河南內(nèi)黃縣城關(guān)鎮(zhèn)發(fā)現(xiàn)的一方清康熙十年(1671年)《呂叔簡(jiǎn)刑戒八章》碑與《刑戒》內(nèi)容一致,足見地方官問案之依賴程度,更是刻石立碑,以戒來者。(李克玉:《呂坤〈刑戒〉流布略考》,載《廣東第二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6年第4期)明末清初人董含(1624—1697年)《三岡識(shí)略》收錄的呂坤《刑戒》一書,僅將“五莫輕打”刪減成“三莫輕打”。在董含看來,宗室和官員可以刑訊,不必有所忌諱,比呂坤更激進(jìn)。同樣是明末清初人趙吉士(1628—1706年)《寄園寄所寄》收錄的《刑戒》則將“五莫輕打”增加至“八莫輕打”,更加小心地將童生、舊族名門子弟、援例等項(xiàng)生員也作為“莫輕打”的對(duì)象,比呂坤更謹(jǐn)慎。同時(shí),還增加了一個(gè)類別,即“五禁甚于打”:“小事用夾棍甚于打,夜間用刑甚于打,決責(zé)不如法甚于打,濫禁淹禁甚于打,重罰甚于打。”“禁甚于打”的前兩項(xiàng)尚屬于用刑,尤其是“夜間用刑”是呂坤所沒有考慮到的;后三項(xiàng)顯然超出了刑訊的范疇,但是給承刑人帶來的痛楚卻遠(yuǎn)大于刑訊。此三項(xiàng)并非趙吉士所處時(shí)代之獨(dú)有,他將其列入《刑戒》肯定是希望把依賴刑訊的三大審判基本要求——“依法裁決、速裁速?zèng)Q、平允裁決”也作為戒律加以重申,便于嚴(yán)格執(zhí)行。
董含和趙吉士的不同態(tài)度既是代表個(gè)人的,也是代表時(shí)代的。在明清交替之際,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明代制度遺產(chǎn)可謂見仁見智,但基本的刑訊技術(shù)方案還得參考呂坤的《刑戒》,這顯然已經(jīng)成為當(dāng)時(shí)司法領(lǐng)域的共識(shí),畢竟獄訟之成敗關(guān)鍵在于能否嫻熟地巧妙地刑訊。清乾隆年間陳宏謀的《五種遺規(guī)》將《刑戒》收錄并以“遺規(guī)”的形式希望后人繼承發(fā)揚(yáng);道光年間徐棟所編的《牧令書》亦輯錄了《刑戒》,影響甚廣;同治年間胡文炳在編纂《折獄龜鑒補(bǔ)》時(shí)便將《刑戒》置于篇首,自言:“即以為折獄者之凡例云。”之所以將其作為“凡例”,皆是因當(dāng)時(shí)問案還是以刑訊為憑借,故而茲事體大,正如《實(shí)政錄》所言:“邇來鞫獄,只恃嚴(yán)加考掠一法耳,果自信無冤民乎?……夫決獄弗慎,有司之罪。”
《刑戒》的同類比較與異同分析
萬歷二十年(1592年),以《寶坻政書》聞名于世的袁黃經(jīng)由京東寶坻(今屬天津市寶坻區(qū))縣令擢升為兵部職方司主事,適倭寇侵略朝鮮,與呂坤所涉的“朝鮮之議”同為一事。在該場(chǎng)戰(zhàn)事中,袁黃遭誣陷而削職,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三月離職。《寶坻政書》成書于袁黃離開寶坻五六年之后,故而在呂坤《刑戒》一書之后。然《寶坻政書》卷六《刑書》并未將《刑戒》收入,原因或是該書由袁黃的弟子劉邦謨、王好善編輯,主要是袁黃為政期間的公文、告示、政令和案卷等,為的是如實(shí)反映袁黃的治理功業(yè)。
處江湖之遠(yuǎn)的縣令遇到的用刑難題,以天津?qū)氎鏋榇淼牡貐^(qū)主要表現(xiàn)為刑具違制和濫用。袁黃“初至本縣之枷有重七八十斤者皆棄去不用,依律造二十斤之枷”,且視情節(jié)輕重,刑具不可濫用:夾棍系詢刑,非強(qiáng)盜不得妄用。針對(duì)當(dāng)時(shí)行刑“五板一換人”的通弊,袁黃規(guī)定“用刑雖多,不許換人”,且遵循“宜少不宜多”的原則,“故堂上刑不常用。即用,三板五板足以示懲矣”,總體按照“慎用刑,常終日不笞一人,經(jīng)月不擬一罪,縣中刑具,皆依律改正。民有犯罪者,必反復(fù)曉諭,令其悔悟”的方針執(zhí)行,重申了明代所倡的“明刑弼教”——“主威之道,不在刑罰,而在威儀。”在袁黃看來,刑名之事有四要:“一曰以求生為主,二曰以原情為據(jù),三曰以名義為教,四曰以案牘為跡。”呂坤的《刑戒》正是從技術(shù)上來實(shí)現(xiàn)“求生”和“原情”的。就此而言,袁黃無非是對(duì)此前明代司法和用刑理念與制度的重新強(qiáng)調(diào)和執(zhí)行而已,當(dāng)時(shí)的多數(shù)官員往往會(huì)打著太祖“明刑弼教”的旗號(hào)濫刑,呂坤譏之謂“御世之術(shù)窮矣”,故而袁黃著眼于重新闡釋“明刑弼教”的實(shí)踐方式。基層治理的目標(biāo)還是在于教化,袁黃的主要策略在于對(duì)官員提倡記功過格加以教化,對(duì)百姓則勸人積善改過,以治心來強(qiáng)化自我修養(yǎng)。在袁黃任寶坻知縣的萬歷十六年(1588年),呂坤出任山東參政,當(dāng)時(shí)他也認(rèn)為“五刑不如一恥”,且認(rèn)為民風(fēng)應(yīng)從兒童抓起,于是設(shè)立社學(xué),頗重啟蒙教育。其父呂德勝已著有《小兒語》《女小兒語》(各一卷)等兒童啟蒙讀物,頗受歡迎,呂坤又作《續(xù)小兒語》(三卷)和《演小兒語》(一卷),尤其是《演小兒語》乃史上最早的兒歌集,利用包括河南、山西、山東、陜西等地民間流傳的46首兒歌為訓(xùn)蒙之用,寓教于樂,是為“理義身心之學(xué)”。這一辦法雖更實(shí)用,但與袁黃的思路異曲同工。
不久,呂坤便成為執(zhí)掌晉陜的地方大員,更需要從具體而微的細(xì)節(jié)技術(shù)上來指導(dǎo)更大范圍的下級(jí)官員實(shí)心用事,這與袁黃所處的一縣之獄不可同日而語,此乃高級(jí)官員和基層官員在對(duì)待政事上的不同立場(chǎng)和身處的地理環(huán)境所致。呂坤也在萬歷二十年進(jìn)入中央,先后在都察院和刑部任職,身處廟堂之高,更能認(rèn)清用刑之奧秘,且更有職責(zé)和使命在用刑的經(jīng)驗(yàn)推廣上更進(jìn)一步,這是呂坤的《刑戒》與袁黃的《寶坁政書》在治理濫刑策略上不同的主因。
袁黃面對(duì)的只是一縣之難題,而呂坤需要考慮的是全局之改觀。尤其是在晚明濫刑的“亂世”,已經(jīng)在沒有時(shí)間等待教化之效,他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需要“下猛藥治積久之弊”,以32條的直白戒律試圖改變?nèi)珖坦佟奥允钦撸潭宦收撸《蛔⒁庹撸瓒粖^力者,相應(yīng)以虛文而實(shí)之不務(wù)者,才短而智慮不足者,庸軟而為左右所用者,識(shí)昏而為左右所蔽者……”“滅紀(jì)法以樹私交,怠職業(yè)而相玩愒,工機(jī)械而丑誠直……”等惡習(xí)。以刑訊為能是在下者驕橫的表現(xiàn),放任下官濫刑則是在上者柔懦的明證,故呂坤主張以剛猛矯柔懦。(張學(xué)智:《呂坤對(duì)晚明政弊的抉發(fā)及其修身之學(xué)》,《中國哲學(xué)史》2009年第1期)《刑戒》又可以視作呂坤政治剛猛的體現(xiàn),戒律性的技術(shù)要點(diǎn)顯然比袁黃在寶坻以德行為范的教化更為剛硬。
(作者單位:山西省委黨校政治與法律教研部;廣州商學(xué)院法學(xué)院)
想爆料?請(qǐng)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四強(qiáng)工程”助力青年干警成長
- 山東省鄒平市檢察院舉辦“醴泉擷英”主題沙龍活動(dòng),聆聽新時(shí)代文明實(shí)踐中心工作人員介紹剪紙文化。該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溫健介紹,檢察工作...[詳細(xì)]
- 檢察日?qǐng)?bào) 2022-09-30
9月16日,山東省煙臺(tái)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隊(duì)民警救助水中拋錨車輛
- 9月16日,山東省煙臺(tái)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隊(duì)民警救助水中拋錨車輛。許靜攝[詳細(xì)]
- 人民公安報(bào) 2022-09-30
群眾通過趣味項(xiàng)目開展技能比武
- 本次社區(qū)運(yùn)動(dòng)會(huì)項(xiàng)目設(shè)置豐富多彩,“抱球繞桿”“袋鼠跳”“瘋狂趾壓板”等六個(gè)趣味項(xiàng)目輪番登場(chǎng),吸引了來自臨朐縣城關(guān)街道和各體彩站點(diǎn)的...[詳細(xì)]
- 中國體育報(bào) 2022-09-30
天津隊(duì)獲全國女排錦標(biāo)賽冠軍
- 本報(bào)訊2022全國女排錦標(biāo)賽9月28日在福建漳州體育訓(xùn)練基地落下戰(zhàn)幕。天津女排在決賽中戰(zhàn)勝江蘇女排,獲得冠軍。江蘇女排雖然奮起追趕,但大...[詳細(xì)]
- 中國體育報(bào) 2022-09-30
排超聯(lián)賽公布新賽季競(jìng)賽規(guī)程
- 本報(bào)訊中國排球協(xié)會(huì)9月29日正式公布了2022-2023中國排球超級(jí)聯(lián)賽競(jìng)賽規(guī)程。新賽季聯(lián)賽將從今年10月下旬至2023年1月中旬舉行。在疫情防控常...[詳細(xì)]
- 中國體育報(bào) 2022-09-30
多彩健身活動(dòng)扮靚國慶假期
- 國慶假期,全國多地將結(jié)合節(jié)慶,開展全民健身賽事活動(dòng),其中既有已成功舉辦十余年的品牌賽事活動(dòng),如大連國際武術(shù)文化節(jié),也有創(chuàng)立時(shí)間不長...[詳細(xì)]
- 中國體育報(bào) 2022-09-30
各地喜迎國慶 一起快樂健身
- 劉晨鄧紅杰黃璐超張軍史文平宋耀武金秋十月,舉國歡慶,全民健身,喜迎盛會(huì)。全國各地廣大群眾以健身的方式歡度國慶,共抒愛國情懷。天津由...[詳細(xì)]
- 中國體育報(bào) 2022-09-30
研學(xué)旅游讓脫貧戶就業(yè)不愁
- 本報(bào)訊(通訊員陳玉立)“我們家現(xiàn)在是脫貧享受政策戶,我在七彩農(nóng)場(chǎng)研學(xué)小鎮(zhèn)打掃衛(wèi)生,一個(gè)月600元。有研學(xué)團(tuán)隊(duì)過來了,我在這兒做保潔;...[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2-09-30
首屆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產(chǎn)業(yè)工人創(chuàng)新交流大會(huì)在魯舉行
- 本報(bào)訊(記者鄭莉田國壘)在黨的二十大即將勝利召開之際,首屆黃河流域生態(tài)保護(hù)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產(chǎn)業(yè)工人創(chuàng)新交流大會(huì)9月29日在山東舉行。陳剛...[詳細(xì)]
- 工人日?qǐng)?bào) 2022-09-30

新華社聚焦第八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山東深耕文化“兩創(chuàng)” 賦能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
- 今天出版的《新華每日電訊》在第7版刊文《山東深耕文化“兩創(chuàng)” 賦能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點(diǎn)贊文化大省山東強(qiáng)化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研究闡發(fā)、保護(hù)傳承...[詳細(xì)]
- 齊魯網(wǎng) 2022-09-30

《人民日?qǐng)?bào)》點(diǎn)贊山東非遺保護(hù)與傳承工作:讓非遺綻放更迷人光彩
-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qǐng)?bào)》在第5版以《讓非遺綻放更迷人光彩》為題刊發(fā)評(píng)論文章,點(diǎn)贊山東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傳承工作。[詳細(xì)]
- 齊魯網(wǎng) 2022-09-30
中山路城市記憶館開館暨歷史城區(qū)文博展館推介發(fā)布會(huì)召開
- 9月29日,中山路城市記憶館開館暨歷史城區(qū)文博展館推介發(fā)布會(huì)在青島市市南區(qū)中山路舉行。歷史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一座城市的歷史是由諸多重...[詳細(xì)]
- 中國日?qǐng)?bào)網(wǎng) 2022-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