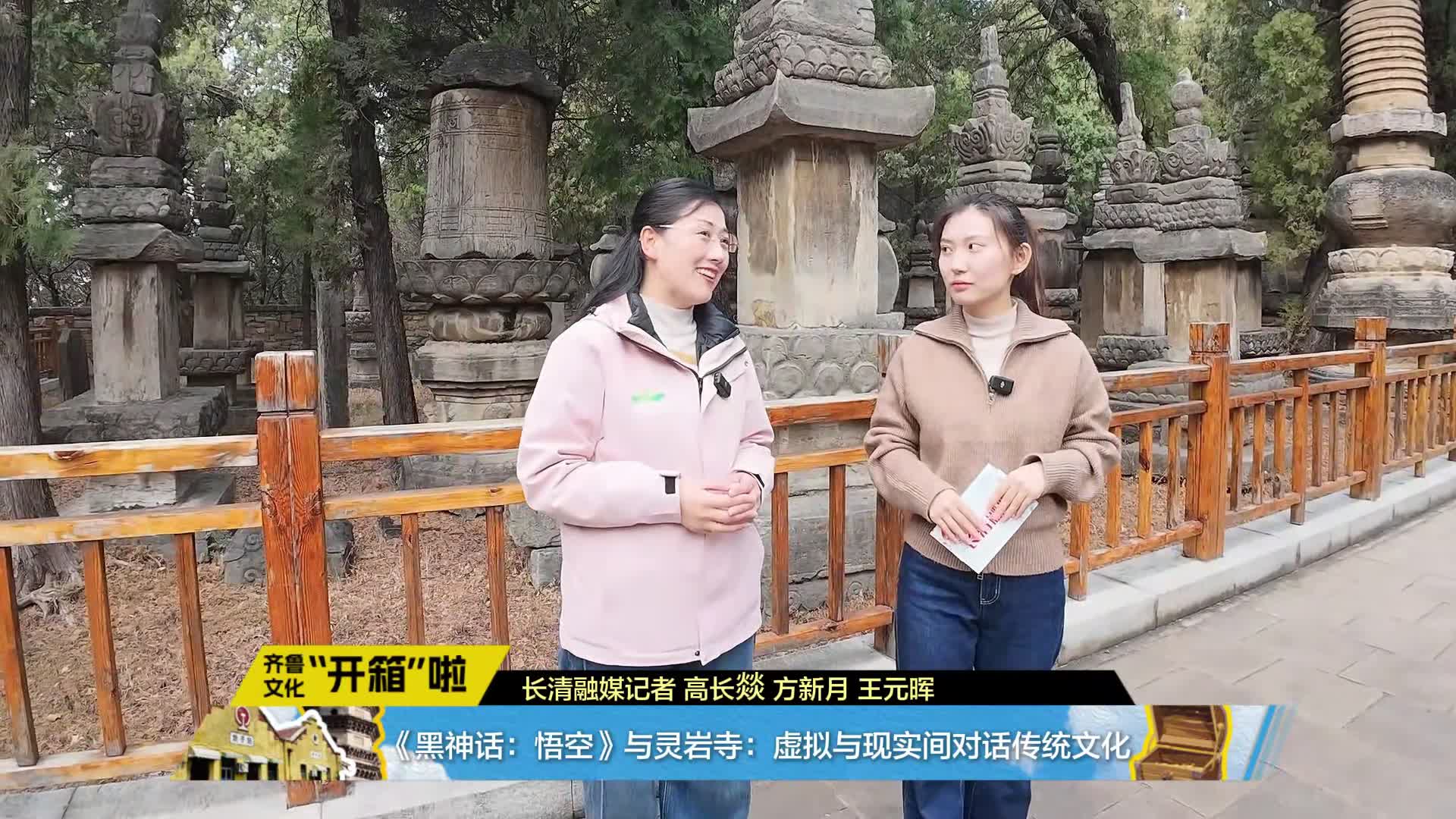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書寫制度初探
來源:光明日報
2025-03-10 09:27:03
原標題: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書寫制度初探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書寫制度初探
來源:光明日報
湖北荊州王家嘴798號戰國楚墓竹簡《詩經》,是早期《詩經》文獻的最新重要發現。該批竹簡總計約300支,內容涵蓋傳世本《詩經·國風》部分。《江漢考古》雜志2023年第2期刊出蔣魯敬、肖玉軍二先生《湖北荊州王家嘴M798出土戰國楚簡〈詩經〉概述》(以下簡稱《概述》)一文,就竹簡形制及簡文內容作了初步介紹。其中有關竹簡書寫制度的部分,對于認識《詩經》的成書及流傳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以下試從三個方面論述。
第一,篇末尾題。據《概述》,王家嘴簡《詩經》分篇書寫,篇末有橫貫簡面的方形墨塊標識,且書有固定格式之尾題。如“《燕燕》六言四章成篇”,“《出其》六言三章成篇”,分別對應傳世本《邶風·燕燕》與《鄭風·出其東門》二篇。王家嘴簡《詩經》的尾題制度,與傳世本《詩經》高度相似,而與已知其他出土戰國《詩經》文獻不同。
傳世本《詩經》各篇篇末皆有尾題,注明全篇章數與各章句數。如《關雎》尾題“《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據陸德明《音義》,五章是鄭玄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孔穎達《正義》據鄭玄《六藝論》“未有若今傳訓章句”之說,認為“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題,或在其后,人未能審也”,指出章句的辨析出自毛公甚或其后。王家嘴簡《詩經》出現之前,已知文獻皆與孔疏上述結論不相違背。2019年刊出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詩經》,存詩57篇,諸篇之間以方形墨塊為區隔,無篇末尾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出阜陽漢簡《詩經》篇末尾題格式為“篇名+字數”,如《豳風·七月》尾題“此右《七月》三百八十三字”(胡平生《阜陽漢簡〈詩經〉簡冊形制及書寫格式之蠡測》,見《阜陽漢簡詩經研究》),無章數句數之說明,僅統計字數。我們知道,篇末字數統計,他類文獻亦不乏其例。武威漢簡《儀禮》九篇,其中七篇篇末記有“凡若干字”之說明,如《士相見禮》尾題“凡千二十字”(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見《漢簡綴述》)。馬王堆帛書《易傳·衷篇》尾題“衷二千”,廖名春先生認為乃字數之統計而有訛誤者(《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見《帛書〈周易〉論集》)。而同時統計章數及句數,則系《詩經》文獻的特有制度。東漢熹平石經、敦煌《詩經》殘卷等皆書尾題,注明章句,與傳世本《詩經》格式相同。西漢海昏侯簡《詩經》,尾題“(某篇)若干章章若干句凡若干句”,如“《既醉》八章章四句凡三十二句”(朱鳳瀚《海昏竹書〈詩〉初讀》,見《海昏簡牘初論》),與傳世本小異而大同。諸種皆西漢以后文獻。至于戰國《詩經》寫本書篇末尾題,王家嘴簡《詩經》之前,乃絕無聞知者。王家嘴簡《詩經》的出現,表明今傳《詩經》尾題形式的直接來源,至少可上溯至戰國晚期早段。《孔疏》將章句的離析推定至毛公時代甚或其后,看來是不正確的。
第二,“篇”“章”“言”三級概念的使用。傳世本《詩經》各篇分為篇、章、句三個基本單位,是《詩經》文本的基本概念框架與解說基礎。由前引可知,這一制度至晚于王家嘴簡《詩經》時代已經確立,并以術語方式呈現。下面首先討論“言”與“篇”。
前引王家嘴簡《詩經》“《燕燕》六言四章成篇”,“六言”,相當于傳世本之“六句”。孔穎達《毛詩正義》在《關雎》篇尾題疏語中指出:“‘句’則古者謂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也。”西漢時期依然沿用此概念。海昏侯簡《詩經》“目錄簡”:“詩三百五篇 凡千七十六章 七千二百七十四言”,所說“言”,即為“句”,與王家嘴簡《詩經》及孔疏所引諸例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海昏侯簡《詩經》正文部分又使用“句”這一概念,與目錄簡用“言”不同。如“《匪風》三章章四句凡十二句”。“言”“句”并用,或表明海昏侯簡《詩經》源自多種文本傳統。
“篇”作為《詩經》學術語,已見于傳世文獻。《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其中“篇”的概念,與今天所使用者相同。其他出土《詩經》文獻,阜陽漢簡《詩經》S144“十二篇”(胡平生先生推定為《唐風》尾題),海昏侯簡《詩經》“三百五扁(篇)”,皆稱“篇”,與傳世本相同。安大簡《詩經》于諸國風詩末尾統計篇數,然不書“篇”字,如“《周南》十又一”。王家嘴簡《詩經》風末尾題尚未披露,然據篇末尾題可知,當時已使用“篇”這一概念,且其內涵與今所通行者一致。王家嘴簡《詩經》“篇”字的寫法值得注意。該字上從竹,下半所從又見于郭店簡《老子甲》簡1(見圖1),讀為“絕智棄辯”之“辯”。裘錫圭先生認為其字系“鞭”字古文,“鞭”“辯”聲近義通。此字郭店簡中多用為“辨”“辯”,又或相當于傳世本之“偏”。(《郭店楚墓竹簡》)王家嘴簡《詩經》“篇”字的寫法,當有助于進一步梳理《詩經》相關概念的源流問題。
第三,章題與章次。王家嘴簡《詩經》章末有題記,注明章次。《概述》:“每一篇除第一章不作提示,其余各章均有明確的分章標注,如第二章就用‘其二’,第三章就用‘其三’,第四章就用‘其四’。”從《詩經》學史的角度看,“章”的概念出現已久。先秦文獻如《左傳》等載卿士大夫外交賦詩,即多稱引某詩之某章。然而作為《詩經》文本的章題制度,長期以來,只能追溯到東漢末年的熹平石經。阜陽漢簡《詩經》及安大簡《詩經》均無章題。近年海昏侯簡《詩經》的出土,表明西漢中期已有此制,即于章末書以“其幾”,標示分章及該章所在位次。基于海昏侯簡,人們一度認為,章題的出現是漢代以來經學建構的結果,并非早期形態。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書有章末尾題,明記章次,則從文獻學的角度將章題制度上推到戰國時期。這一發現具有重要的《詩經》學意義。它表明,確定的章次及其說解,應是早期《詩經》傳授的基本內容。
上述傳授制度,傳世及出土文獻皆有線索可尋。《左傳》昭公元年晉樂王鮒“《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昭公四年魯申豐“《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及前《孔疏》所引定公十年郈工師駟赤“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皆稱說章義。上博簡《孔子詩論》謂《關雎》“其四章則喻矣”,“《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禮”,論說特定章次的具體意義。凡此皆為前述《詩經》學傳授方式的承繼與反映。虞萬里先生根據《左傳》等傳世文獻所載,“上推西周國學教授《詩》時也已用‘章’”(《章句起源與初期形態蠡測——以安大簡、阜陽簡、海昏簡〈詩經〉為中心》)。從《孔子詩論》的稱述章旨及王家嘴簡《詩經》的章題制度來看,這一論斷應是可信的。需要指出的是,按虞先生的觀點,《詩經》的分章說解是源于西周王官之學的教授傳統,那么,確定的章次次序也應該是必須的。否則,賦詩活動中所謂“首章”“卒章”“二章”“三章”云云則失去意義。部分詩篇章次異次現象的存在,似不足以說明原本章次的不確定,我們曾從訓詁入手并結合《詩經》書寫體例試作討論(《安大簡〈殷其雷〉篇的章次類型與〈詩經〉的敘事邏輯》)。對此問題應做更進一步的細致梳理和深入分析。
總之,荊州王家嘴簡《詩經》提示人們,早期《詩經》的文本傳承呈現出相當的規范性,其文本內容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安大簡《詩經》諸篇除字形差異外,其具體內容基本同于傳世本。《七月》是《詩經》中有數的長篇之一,凡八章章十一句,三百八十三字。阜陽漢簡《詩經》所記《七月》字數,與之完全相同。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用諸子類文獻的文本流變推演《詩經》等經典文獻的成書規律,過于強調漢代學術對《詩經》經典地位的建構作用,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高中華,系聊城大學文學院講師)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數字+中醫藥”大有可為
- 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政府副秘書長、鄭州航空港區管委會主任田海濤表示,隨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應用,數智化成為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和發...[詳細]
- 經濟日報 2025-03-10
搶抓“兩新”機遇擴內需
-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棗莊市委書記張宏偉表示,內需是經濟發展...[詳細]
- 經濟日報 2025-03-10
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能
- “推動創新優勢轉變為發展勝勢,關鍵在于科技成果的高效轉化應用,切實用科技創新的‘關鍵變量’催生高質量發展的‘最優增量’。”山東省棗...[詳細]
- 人民日報 2025-03-10
全方位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千方百計推動農業增效益、農村增活力、農民增收入,這其中鄉村產業發展是關鍵之舉。地處魯西平原的山東聊城是典型...[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3-10
積極發展深遠海養殖 向海洋要食物要效益
-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扶持畜牧業、漁業穩定發展”“全方位開發食物資源”“大力發展海洋經濟”。深遠海養殖是樹立大食物觀、向海洋要...[詳細]
- 農民日報 2025-03-10
多方協作形成維護國防利益的強大合力
- 于安玲代表本報北京3月9日電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濟寧市鄉村振興事務中心副主任于安玲告訴記者,最高檢工作報告中堅決維護國防利益和英雄烈...[詳細]
- 檢察日報 2025-03-10
我眼中的《青春之光》
- 2023年9月13日,離第十二套義務教育教材正式送審還有不到兩天的時間,作為教材責編的我,終于拿到了經作者本人、教材編委會和編輯室老師們...[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10
積極探索科產教融合發展模式
- 青島農業大學建設國家一流本科課程“農業經濟學”,通過引入產業教學資源,采取“教”與“學”主體組織化、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對話分...[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10
準備充分才能提高評課質量
- 組織跨學校的聽評課活動,是各學科教研員經常做的一項常規工作。筆者認為,教研員應做好三方面準備 第一,調研學校的本學科教學進度,了解...[詳細]
- 中國教育報 2025-03-10

央視《新聞聯播》播發住魯全國人大代表關志潔兩會聲音:加大種業創新力度
- [詳細]
- 閃電新聞 2025-03-09

全國人大代表李蘭祥:聚焦高質量發展 四個“更大力度”抓落實
-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泰安市委副書記、市長李蘭祥。”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泰安市委副書記、市長李蘭祥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表...[詳細]
- 人民網山東頻道 2025-03-09
讓“志愿者的微笑”成為“中國名片”
- 本報訊記者蒲曉磊“我們看到青年志愿者群體在服務社會、引領青年、促進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請問志愿服務中有哪些感人故事。”在3月7...[詳細]
- 法治日報 2025-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