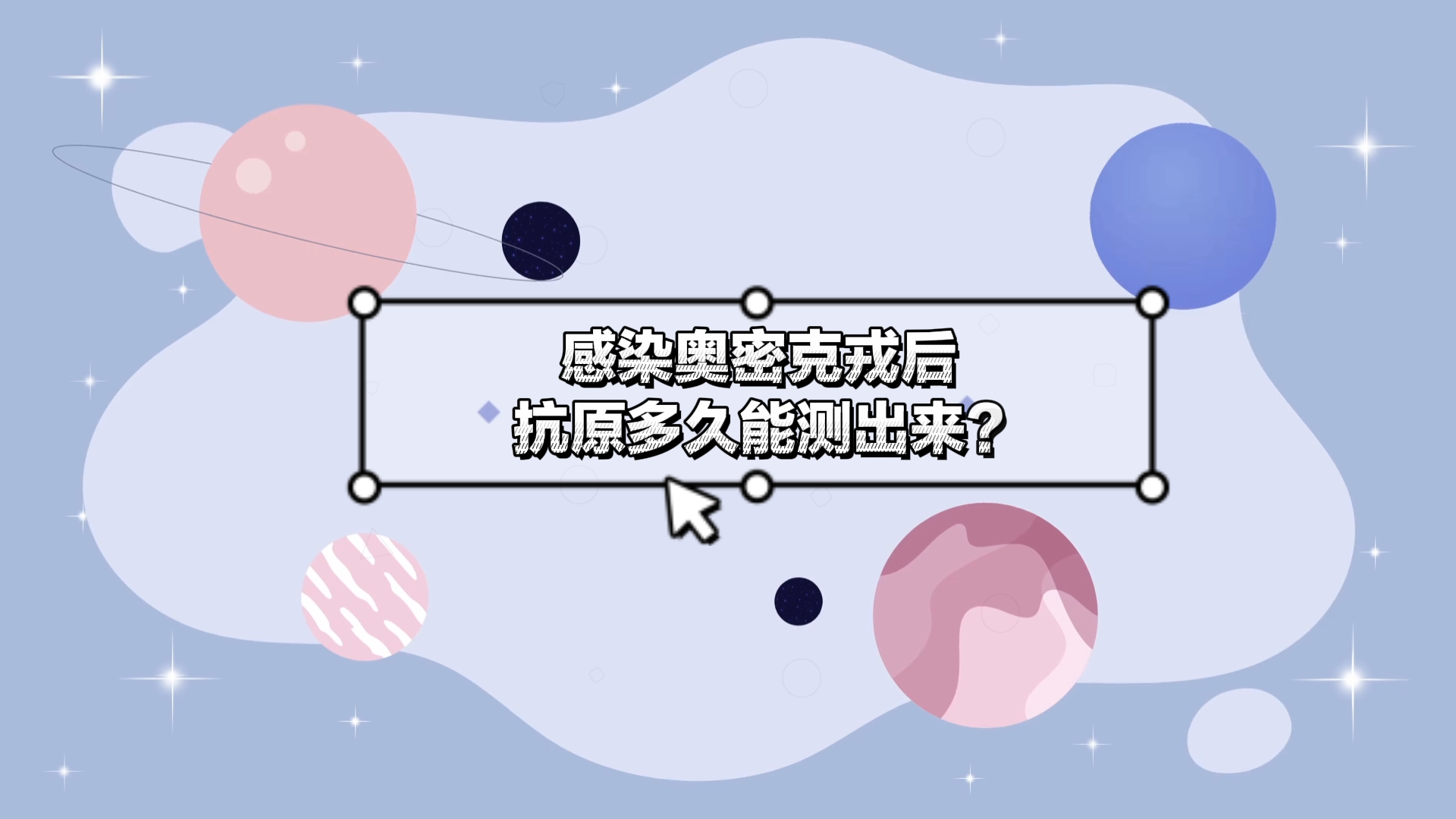消失的古城墻:“櫟陽”無人識商鞅
來源:法治日報
2022-12-16 10:51:12
原標題:消失的古城墻:“櫟陽”無人識商鞅
來源:法治日報
原標題:消失的古城墻:“櫟陽”無人識商鞅
來源:法治日報
□ 余定宇
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述:商鞅在魏惠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因而挾了一部李悝所編的《法經》逃去秦國,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商鞅在贏得秦孝公的信任而在秦國推行變法之前,恐怕自己的聲望不能服眾,于是,便效仿了吳起的計謀設計了一個小小的把戲——“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并懸賞重金,招募民眾把這根木頭搬到北門。有位市民,半信半疑地把這件事情做了,商鞅果然爽快地賞給他“五十金”。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傳得整個秦國沸沸揚揚,而商鞅也借此在秦人心目中,迅速地樹立起了一個“信賞必罰”的權威形象。
考諸秦史,秦人的祖先在東進過程中,曾先后在關中盆地上建立過五六座都城。而司馬遷《史記》中所說的這座“國都南門”又究竟在哪里呢?史學界只知道,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商鞅變法”,但卻不知道,商鞅第一次變法時所在的那個秦國國都,既不在雍州,也不在咸陽,而是在那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櫟陽。
西周時候,秦人的祖先是甘肅南部一個由“殷商遺民”而西遷的游牧民族。自東周初年,秦人的首領因抗擊犬戎有功而被分封為諸侯國之日算起,這個昔日從“東夷之地”被放逐到“西戎之角”的野蠻部族,才又一次登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而其后,驍勇的秦人便開始像潮水般地翻越隴山,殺入關中,用他們的青銅刀劍和戰車,從犬戎的手中,奪取了原先屬于西周的寶雞、鳳翔、岐山等大片土地。到那位能征慣戰、被史書稱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時代,秦國的版圖已一度遠伸至西北的青海湖邊、祁連山下,成為中國西部一個雄霸一方的霸主。
秦穆公去世之后,經過一段兩百多年的平庸歲月,為了收復被魏國搶走的“河西之地”,秦獻公在即位的第二年便把國都從雍城(今日鳳翔)東遷到櫟陽,其目的不僅僅是要恢復“飲馬黃河”的秦人舊夢,亦隱隱然已含有一種欲與山東六國“逐鹿中原”的巨大雄心了。獻公死后,孝公即位,為了一洗“諸侯會盟,不與秦國”的恥辱,其那種“欲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復仇野心,更是路人皆知。要通過什么樣的方法,才能夠更迅速地“富國強兵”?正當秦孝公為此問題而傷盡腦筋時,那位魏國的小吏公孫鞅(即后來的商鞅),恰好挾著一卷《法經》來到了櫟陽。
實事求是地說,商鞅是中國古代一個性格很復雜的歷史人物。而“商鞅變法”,亦不是他個人命運的悲喜劇。這場改革,雖美其名曰“變法”,但它的內容卻已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法律”的范圍,而更多的是涉及那些關于國家政治體系結構、制度、政策等政治性的東西。“商鞅變法”對后世影響最重大的,概括起來主要是這三個方面:第一,君主專制下的“官僚政治”開始興起;第二,“重農抑商”的社會傳統政策開始形成;第三,中國法律史上的“重刑主義”開始抬頭。
平心而論,在“商鞅變法”的諸多改革內容和歷史影響之中,既有“鉗民之口”“殺人如麻”等壞的一面,也有“獎軍功、獎耕織”和“車同軌、書同文”等好的一面,既有開啟野蠻的一面,亦有推動進步的一面。但他最難辭其咎的便是:他在中國的法律制度史上,首開了一種“重刑主義”的先河。他把一個國君的治國之道簡化為“刑賞”二字,將人民的命運簡化為“耕戰”二字,從而,使秦人一生的生活內容,全部被壓縮為“耕田”和“打仗”這兩件事。他使法學淪為了政治的附庸,使法律變成了官僚的打手,而將“戰爭”與“刑罰”當成了秦國崛起的動力。通過商鞅的十年變法,秦國的“國”確實是“富”了,“兵”也確實是“強”了,但秦國也由此開始,迅速走上了一條萬劫不復的自我毀滅的道路。
由此可見,“以刑治國”與“依法治國”之間,真的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回首歷史,昔日的一切都恍如過眼云煙。而細思當年,商鞅究竟是在為誰而變法?為什么而變法?他又究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功臣還是一大罪人?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自秦始皇橫掃山東六國、統一中國之后,中國古代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便染上了一種濃重的、從秦國傳入的血腥味。
(文章節選自余定宇《尋找法律的印跡(2):從獨角神獸到“六法全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濟寧二十里鋪街道金牌調解化糾紛
- 本報訊今年以來,山東省濟寧市任城區二十里鋪街道選聘老黨員、老干部、退休教師、法律工作者擔任金牌調解員和信訪代理員,試點打造“金牌調...[詳細]
- 法治日報 2022-12-16
青島黃島交警借力科技減少交通事故
- 本報訊記者曹天健通訊員馮希軍今年以來,山東省青島市公安局黃島分局交警大隊巧用科技警力,大大減少了道路交通事故發生。黃島公安分局交警...[詳細]
- 法治日報 2022-12-16
山東濟南市:智能化農機讓豐產更“智慧”
- 聯合收割機不用駕駛員,只需要在程序上設置好路徑,農機設備就可以自己完成水稻收割。近日,在山東省濟南市高新區臨港街道胡家岸水稻種植合...[詳細]
- 農民日報 2022-12-16
增強基層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 筑牢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
-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要求“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有效實現黨的領導的堅強戰斗堡壘”,闡明了基層黨組織在...[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2-16
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 黨的二十大之后,習近平主席首次出訪選擇東盟國家,出席G20峰會、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并分別與印尼和泰國兩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一致...[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2-16
新增14地開展二手車出口業務
- 新華社北京12月6日電(記者謝希瑤)記者6日從商務部獲悉,商務部、公安部、海關總署近日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擴大開展二手車出口業務地區范圍...[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2-16
山東建立重型柴油車“黑白名單”制度
- 本報訊為減輕移動源排氣污染,山東省生態環境廳、省公安廳日前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重型柴油車遠程監控有關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詳細]
- 中國環境報 2022-12-16
曲阜厚植綠色動能塑造發展優勢
- 本報訊“近年來,曲阜市以推動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為抓手,堅持‘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厚植綠色動能,塑造高質量發展新優...[詳細]
- 中國環境報 2022-12-16
環評可成為助企發展的朋友
- ◆殷明勵項目環評是當前改革力度大、創新舉措多、成效明顯、企業關注的領域。湖北實行環評并聯申報審批,陜西實行項目環評即受理即評估、評...[詳細]
- 中國環境報 2022-12-16
黃河國家戰略研究院智庫成果發布
- 科技日報訊(記者王延斌)通過遙感技術和地理信息系統技術解譯黃河三角洲地區的植被信息,搜集、獲取該區域重要的環境變量,可為黃河流域生...[詳細]
- 科技日報 2022-12-16
“沙漠硅谷”:“云計算”成通往世界“新名片”
- 探訪中國版“沙漠硅谷” “云計算”成通往世界“新名片”。工作人員在中衛西部云基地大數據中心的機房里巡查。,正不舍晝夜地為三星電子、...[詳細]
- 中新網山東頻道 2022-12-16
山東今年開展各類病蟲害防控面積約6.01億畝次
- 12月5日下午,山東省農業技術推廣中心舉行媒體吹風會,通報全省2022年農作物病蟲害發生防控情況,發布2023年農作物病蟲害發生趨勢。全省農...[詳細]
- 中新網山東頻道 2022-12-16
“喚醒”戈壁荒漠 新疆“借光”生金
- 中新社烏魯木齊12月5日電題 “喚醒”戈壁荒漠新疆“借光”生金。初冬,新疆和田地區墨玉縣喀爾賽鎮庫木博依村,冬日的暖陽映照在一排排光伏...[詳細]
- 中新網山東頻道 2022-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