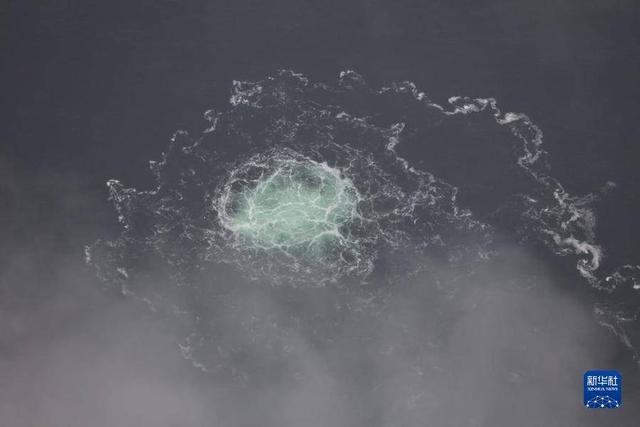棗樹記
來源:光明日報
2022-10-07 06:59:10
原標題:棗樹記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棗樹記
來源:光明日報
我對棗樹寓意的理解,緣于小舅的婚禮。那天,母親塞給我三角錢,交代道,去供銷合作社買半斤紅棗。我將三角錢攥在掌心,狂奔如小馬駒,“嘚嘚”的腳步聲回響在老街的石板路上。古鎮(zhèn)為驛站,一至五甲一條街,從外婆家五甲,跑到三甲火巷張家門鋪,一華里,站在高高鋪搭前,怯生生地說,半斤紅棗。店主一只眼睛壞了,眨著云翳,翻了翻白眼,從玻璃瓶里抓紅棗裝進牛皮紙袋,稱好,遞給我。我雙手抱著半斤紅棗往小舅家跑去,棗香溢滿古街。氣喘吁吁地交給母親,只見母親將紅棗拿了出來,裝進將封口的紅被子,剩余撒在婚床褥子上,喃喃念道,早(棗)生貴子!滿臉悅色。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棗還有如此美好的祝禱。那彌散在故鄉(xiāng)老街的棗香,像迷了魂一樣,使我對紅棗樹有一種天然的敏感與親近。
那個夏日晌午,車入稷山縣萬畝唐棗樹林,那掩埋了半個世紀的棗香記憶,突然被激活、喚醒了。
喊棗魂者歸來。一園漢棗樹、魏晉棗樹,最多的是唐棗樹。放眼望去,樹干黢黑,布滿皺紋,樹心炸裂,被雷劈火燒過后,仍青枝綠葉,青棗綴滿枝頭,碩果累累。每一株猶如天闕玉樹,古樹盤根,遮天蔽日一片陰涼。不由得驚嘆一聲,好大一園古棗林。
古棗樹遮天蔽日,蔚然大觀。我的思緒轉(zhuǎn)至從前,少時讀大先生《秋夜》,開篇就是經(jīng)典妙語:“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后來我長大了,屢去山陰,入百草園,周家后花園里,不見兩棵棗樹的蹤影。大先生秋夜所見棗樹,應該在北平城里。那兩株棗樹,本不屬于南方。
在我的老家云南,也鮮見棗樹。很多年后,我在河南靈寶、甘肅酒泉,見過不少野棗樹,多為荊棘叢,并不像山西稷山縣這一片古棗樹林,老樹枯枝新芽,盤虬野地,軀干枯槁,天火閃電擊過后,寒霜侵身,雪野覆蓋,卻活到了今日,千年不死。
想想我家永定河邊的柴門前,鄰居家院落里也種了一株棗樹,將近十年了,僅小碗口粗。鄰家數(shù)年未住人,無人打理,靠天雨而活。枝頭照樣結(jié)滿了棗,秋天紅成半樹,金風一吹,墜落一地,拾起來,咬著香甜嘎巴脆。去年春夏之季雨少,見葉子發(fā)黃,我以為會干涸而死,誰知一場春雨襲來,葳蕤如昨。
千載如斯,稷山的千年唐棗樹祖,也是這番活法嗎?下車,近棗樹祖情亦怯,我們向一株株古棗樹走去,溯歲月田埂而上。
甘棠井驚現(xiàn)于前,身著漢服、唐裝的棗農(nóng)載歌載舞。“合、四、乙、尺、工”,鼓、镲、鑼、號奏響,胡琴裂帛。我未趕過去湊熱鬧,踏著時光的鼓點,走近唐棗、晉樹,紅棗樹祖兀立曠野,汾黃之間,連林成海。最早的已有1800年,有的要兩三個人伸手相圍才能環(huán)抱。這是一株怎樣的古棗樹啊!接漢風唐月,宋雨元霜,讓人走近時,只想擁抱,只想依偎,只想諦聽她的歷史心跳。很多株古棗樹心枯如井,如鐵,只余下薄薄一層皮,真讓人擔心,倚在樹干上,會轟然倒下。剎那間,心生敬畏和感動。從枝丫縫隙望穹隆,仰天長嘆,生命何其短,摩挲、歌吟過這園老棗樹的文人墨客早化為泥土。千年過去,樹心已被天火燒焦,樹干被劍戟斬斷,可葉脈還在流淌,板棗綴滿枝頭一樹連一樹,一園接一園,在春陽、夏雨、秋風中,笑著,花搖枝顫。
摩挲著那一株株老棗樹祖的皮膚,我的手陡生粗糙感,這種銼痛由皮膚傳入神經(jīng),直抵心脈。無邊的痛后,卻是血一般的奔突,紅棗醬色如血,如火,是煉獄過后的浴火重生啊。一顆、兩顆、三顆、四顆板棗,水煎,煮沸,棗香四溢,水霧冉冉,萬千中藥的苦,皆伴棗性而聚變,而新生。那是痛楚過后的沸騰。誰會想到,一枚枚河東板棗,竟然還是救命之丹。
十年前,至親遽然染疾,幸有名醫(yī)懸壺濟世,妙手還春。治療后,處于恢復期,亦無藥可開。醫(yī)囑說,只需調(diào)理即可,到中醫(yī)院開幾劑中藥吧。后用了一個妙方:蟲草兩根、西洋參十數(shù)片,寧夏枸杞一把,稷山板棗四枚,兌水三四百毫升,陶鍋里煮兩個小時,趁熱喝下,再將所有藥渣嚼服。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喝就是三載,抵抗力大增,惡疾已遠。那一刻,我對紅棗,對河東板棗,有了一種膜拜感,它的功力遠遠超出早生貴子的民間祝福,更兼發(fā)百草之七味,和烈藥之中庸,抑毒藥之暴戾。三四枚板棗一放下去,各種烈藥、苦藥、補藥、瀉藥都中和了,成一服濟民良藥。毒性去,烈性減,補到位,泄不死,苦可口,其要諦正在于一粒粒紅棗的吸納、添減、平衡、調(diào)劑與溫補之功。
發(fā)現(xiàn)板棗有藥補之效的郎中,遠及漢代。首推南陽張仲景,但影響最大的是神醫(yī)華佗。相傳曹操患頭瘋病,寒風一吹就發(fā)作,心亂目眩。華佗巡診,望聞問切后,知道實乃心病——既生瑜,何生亮,既有臥龍崗,何必銅雀臺啊。遂為曹公針灸,瞬間腦清目明。曹丞相高興,欲重賞華佗。華大夫搖頭,說針灸之療,只管一時,不管一世。安邑御棗和烈藥,可除丞相腦疾。
華佗為曹孟德配藥,稷山板棗用得最多。采摘于河東御棗園,運至洛陽城,驛程幾百里。后來,稱帝后的曹丕下詔,問群臣:“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葡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言安邑御棗也。”曹丕不僅是文章大師,也是美食家。南方有嘉木,驛馬馱來的龍眼、荔枝都吃過了,可他覺得不如西域來的葡萄和石榴好吃,味道發(fā)酸,甚至不如中原普通小棗,何論河東安邑御棗呢!
稷山縣屬河東郡,板棗又稱河東棗,漢代就是貢棗,亦叫安邑御棗。太史公云:“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司馬遷故里就在河東龍門,河東一脈,離稷山棗園只有幾十里,他壯游天下前,當來過稷山板棗園,才會將稷山板棗與燕、秦栗子,蜀、漢橘子相提并論吧。板棗與栗、橘一樣,早就列華夏古國的珍品佳肴。江山留勝跡,一棗澤萬代,誰可堪比?民!
河東板棗入藥文獻記載,始見于晉代。南朝陶弘景配藥時,常用板棗為藥引,在《本草經(jīng)集注》中寫道:世傳河東棗特異,與青州、江東、臨沂、金城不同。陶弘景道出了配藥的一個妙方,天下之棗多矣,入藥作引,唯稷山棗甲天下啊。
皇天后土必育御棗。那天踏進河東地界,先祭后土祠。登秋風樓,望河汾交匯處,大河如鏡,清濁分明,遙想漢武帝吟秋風辭。那是公元前113年秋天的事,劉徹率群臣巡游,至河東郡汾陽縣,祭祀后土,擺放的貢果是板棗。皇天后土蒼生命,有糧不慌,有棗更帶來吉祥。時,秋風蕭瑟,鴻雁南歸,登上樓船,泛舟黃河、汾河并流水域。帝宴中流,逝水如斯。文功武略、求仙封禪的漢武帝終于被秋風吹醒了,天下哪有長生不老之藥,御酒喝罷,遂吟《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云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
懷佳人兮不能忘。
泛樓船兮濟汾河,
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fā)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碑文為唐人書丹,行書,是二王書風,魏晉風骨,頗與漢武大帝的心境契合。不知那年司馬遷隨行否?彼時,離太史公辭世僅差兩年。《史記》未收此辭,還好,班固《漢書》為漢家天子歌吟留痕。天上大雁飛過,秋風吹過,百草霜衰,美人無顏色,唯黃河黃花遍地香。
青春幾何?人生豈能不老。漢武帝未承想到,江山、宮闕、扶欄、樓船,雕欄玉砌,都經(jīng)不起兵燹與宮亂。一陣秋風起,唯有遠處的古板棗樹見證了時間、歲月、王朝,千年過盡,依舊生機勃勃,生兒育女,碩果不絕,歷時千載,仍將衰老和死亡攔在棗園之外。
神樹啊。從秋風辭碑前移步樓頂,遠眺黃河與汾河匯合處,水開天境。自盤古開天,三皇五帝,最初祭祀的是“社”,“社”就是土地之神,后土地母。商代以降,祭“社”又加上一個“稷”的儀式。“稷”就是谷神,周代的始祖后稷,封地就在距后土祠不遠的稷山縣,皆屬河東郡。后稷種谷成神,糧安中華萬世。而傳說稷妻則嫁接了千年仍在結(jié)棗的板棗樹。五谷之根,家化萬物,有粟、有麥、有谷、有稗,亦有千年棗樹。江山社稷百姓安,有糧則命安,有棗則福來。
夢斷大河水不盡,何處棗生三晉地。我往熱鬧處走,甘棠井亭前,觀棗農(nóng)們穿漢服唐裝,老翁、老嫗搖轆轱,耕夫和歌。我倚在樹前照相,仿佛是依偎在老祖母的懷里,東風掠過。一陣清涼,一股棗香,是老奶奶樹祖之味,是搖籃之中母親的奶香、棗香。
千年棗樹活著,活在大河之濱。母親河,棗祖樹,老且彌堅,仿佛在喻言華夏子孫繁衍,萬家興旺,江山永固。一河血脈,與千萬株棗樹相連。秋風起兮明月夜,文心如初,元氣依然。
莫道棗樹老,一棗一樹皆成林。
(作者:徐劍,系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長)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wǎng)官方微博(@齊魯網(wǎng))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wǎng)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塞上江南“風景”如何變“豐景”
- 金秋時節(jié),賀蘭山東麓的寧夏銀川市賀蘭縣四十里店村稻漁空間,2600多畝五彩稻田豐收在望。清風拂過,以稻菽為“墨”畫出的巨幅山水畫隨風飄...[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0-07
千年大運河煥發(fā)新生機
- 【江河印象】??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達杭州,全長1960余公里,流經(jīng)北京、河北、天津、山東、江蘇、浙江6個省市,溝通海河、黃河、淮河...[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0-07
【領航中國】把種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 今年我有300畝地用來進行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大豆和玉米分別選的是‘華豆17’和‘登海605’,這倆品種優(yōu)點不少,比如高抗倒、高抗病、高...[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0-07
水木湛清華 奮進新征程
- 十月的清華園,秋色宜人。校園內(nèi),每一方磚瓦、每一株草木,都見證著清華大學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記錄著一代代清華師...[詳細]
- 人民日報 2022-10-07
千年運河 水韻華章(新時代畫卷·江河奔騰看中國)
-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千百年來,運河滋養(yǎng)兩岸城市和人民,是運河兩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護好大運河,使運河永遠造福人民...[詳細]
- 人民日報 2022-10-07
保護好黃河口濕地(人民滿意的公務員)
- 秋季的黃河三角洲河海交匯處,景色壯美。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來東營考察時說 “要把保護黃河口濕地作為一項崇高事業(yè),讓生態(tài)文明理念在...[詳細]
- 人民日報 2022-10-07
千里大運河 清流煥新顏
- 千里運河,溝通南北,貫通古今。4月28日,歷經(jīng)14天集中補水,京杭大運河實現(xiàn)百年來首次全線水流貫通;6月24日,大運河京冀段旅游航道實現(xiàn)互...[詳細]
- 經(jīng)濟日報 2022-10-07

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經(jīng)濟日報》頭版頭條聚焦勝利油田
- 今天出版的《經(jīng)濟日報》在頭版頭條“喜迎二十大”專欄以《構(gòu)建多能互補綠色供給體系 勝利油田確保能源供應安全》為題刊文,點贊中國石化勝...[詳細]
- 齊魯網(wǎng) 2022-10-07

保護好黃河口濕地!《人民日報》點贊山東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工作專班
- 保護好黃河口濕地!《人民日報》點贊山東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qū)工作專班[詳細]
- 齊魯網(wǎng) 2022-10-07
穩(wěn)步前進“越辦越好”
- 穩(wěn)步前進“越辦越好”寫在第五屆進博會倒計時一個月之際(2022-10-06)稿件來源 新華每日電訊新華深讀東海之濱,黃浦江畔。一個月后,全球...[詳細]
- 新華每日電訊 2022-10-06
紓解“急難愁盼”,推動養(yǎng)老服務高質(zhì)量發(fā)展
- 【研究報告】編者按在剛剛過去的重陽節(jié),城鄉(xiāng)社區(qū)、無數(shù)家庭、養(yǎng)老服務機構(gòu)……處處洋溢著敬老愛老的溫馨情愫,“如何讓老人老有所養(yǎng)、生活...[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0-06
我科學家實現(xiàn)百公里自由空間高精度時間頻率傳遞
- 本報合肥10月5日電(記者常河、齊芳)通過發(fā)展大功率低噪聲光梳、高靈敏度高精度線性采樣、高穩(wěn)定高效率光傳輸?shù)燃夹g(shù),我國科學家首次在國...[詳細]
- 光明日報 2022-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