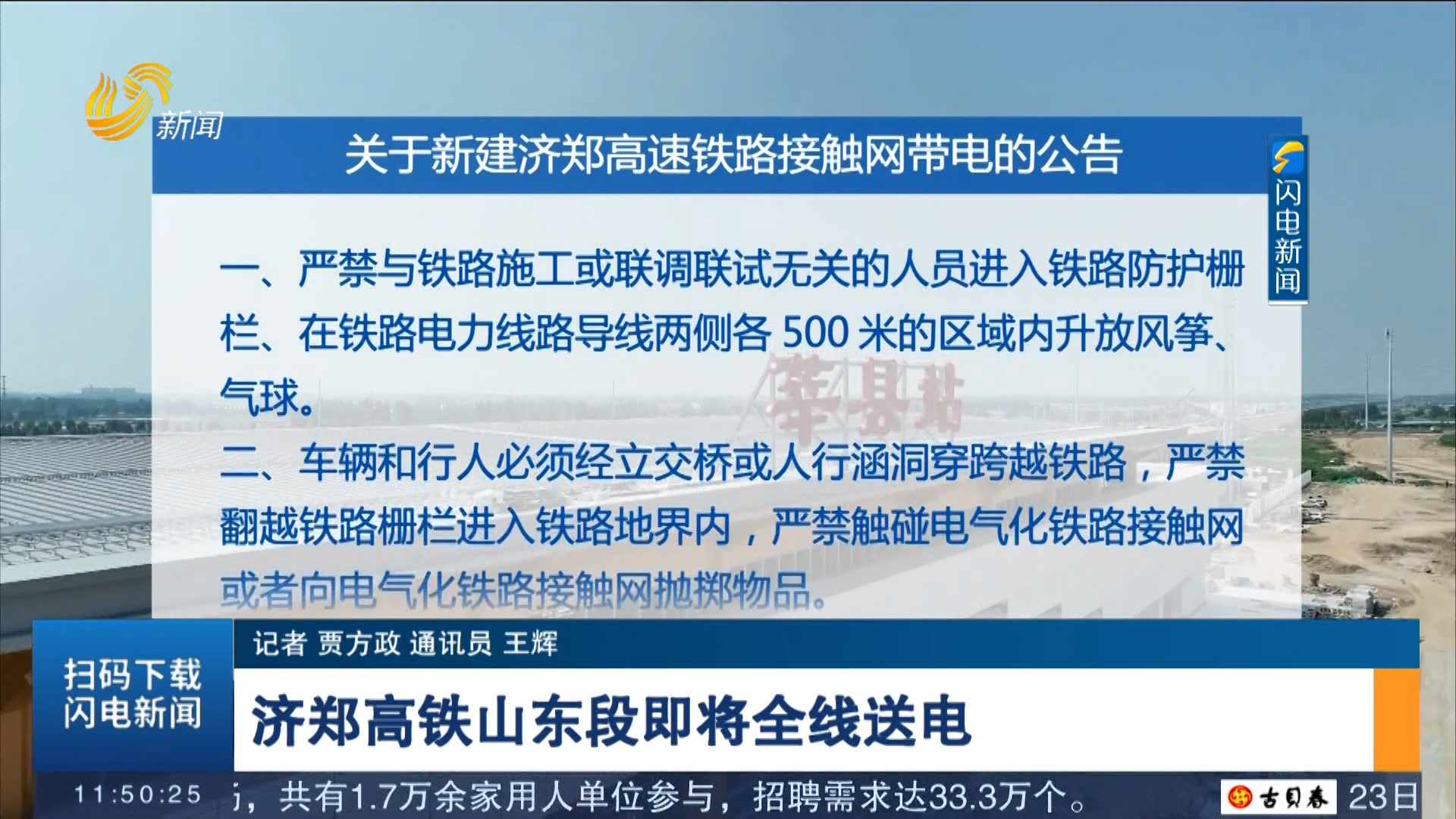《經營地方》呈現城市史研究的“濟寧經驗”
來源:齊魯晚報
2023-08-26 09:41:08
原標題:《經營地方》呈現城市史研究的“濟寧經驗”
來源:齊魯晚報
原標題:《經營地方》呈現城市史研究的“濟寧經驗”
來源:齊魯晚報
歷史學者孫競昊教授的《經營地方:明清時期濟寧的士紳與社會》,是一部以山東濟寧為經驗個例、士紳活動為主線展開的城市史個案研究著作,基本內容來自昔年他在多倫多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中社會史的部分。有別于以往的明清史研究關注點集中在江南地區的情況,該書將研究視野擴展到因大運河興起而繁榮的北方城市濟寧,并注重將江南地區與之進行對比。濟寧士紳在對城市的塑造過程中,展現了地方力量與國家權力的精彩博弈,也通過與“商”這個階級的緊密聯系,呈現出北方城市別樣的城市化進程。
□季東
“植入型”城市化
如同華北平原的一般情形,山東在歷史上長期作為傳統的農業區。但是,元朝時期京杭大運河的出現,開啟了華北平原沿運地帶系列經濟和社會變革。在山東西部,財富和人口向運河兩岸城市、市鎮和初級市場流動,開拓了沿運的城市空間,產生了一個城市化的狹長地帶。
濟寧和臨清曾是明清時期山東最大的經濟中心,至19世紀末才被省會濟南與膠東半島的通商口岸煙臺、青島超過。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饒濟凡將開埠前的明清中國城市分為七個等級,山東省內只有沿運河的濟寧、臨清和離運河不遠的濟南被列入三級城市,而京師北京也只是二級城市。歷史學家鮑德威將19世紀的山東分成四個貿易區,分別以濟寧、臨清、濟南和濰縣為中心,每個城市都有十萬以上的人口。
明清時期,各省一般不存在獨立的商品流通網絡。各個地區或亞地區的經濟,更多的是擁有各自的市場軌道和線路,并匯入全國范圍的貿易體系。然而,由于同一行政區劃的管轄,頻繁、規則的省內交流和交換是可能的。在山東境內,東西部之間的貿易是最重要的商業交換,而東部的半島地區借運河連接到全國商業網絡中。
作為山東的主要地方產品集散中心,濟寧在漕運和運河貿易網絡中具有戰略位置,從而形成在跨區域商品流通中突出的樞紐地位,其南方導向的經濟促進了南北經濟交換。以乾隆時期糧食的長途販運為例,根據研究,山東西南部每年輸出數百萬石的小麥、豆類和雜糧到長江三角洲、直隸、河南,一直持續到清末。
孫競昊教授分析指出,濟寧源自運河運輸和貿易的“植入型”城市化,與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大不相同。在長江三角洲,城市空間的擴張源于本地區的商品化,是內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長江三角洲有比較完備的區域市場結構,星羅棋布的農村集市,市鎮、縣城,州治、府治所在的中心城市構成三級網絡,可以被稱為自身“內生型”的城市化模式。而濟寧的個案顯示,在山東西部,甚至可以說在華北平原的運河地區,原本傳統農業區的城市化,是在缺乏本地農村商品化的情況下發生的。
概言之,《經營地方》認為,明清時期北方運河城市的興起或擴張是國家政策的一個副產品,對國家主導的漕運及運河貿易的依賴,也造成了其“交換”勝于“生產”的寄生性,其外在“植入型”城市化道路,也決定了區域經濟的脆弱性。總的來說,從城市化和城市形態角度看,頗具自身特色的濟寧個案反映出北方運河城市的一般特點。
官紳商一體化
大運河推動了濟寧經濟與生活的商品化和城市化,而在商品化的城市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地方精英則扮演了積極的領導角色。
作為孔孟之鄉,濟寧屬于傳統儒家中心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眾多文士的故鄉。隨著商品經濟和交通通信的蓬勃發展,濟寧成為明清時期中國北方同級政區地方士紳精英人數最多的地方之一。明中葉開始,濟寧人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據康熙年間《濟寧州志》記載,明朝濟寧共計產生243名舉人,其中65人后來考中進士。濟寧科舉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時期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山東乃至整個中國北方居于翹楚地位。
功名及第者的數量,通常與地方士紳權力的強弱相對應。雖然科場上的成功者從官場去職后,才開始在家鄉真正扮演地方領袖的角色,但在官學注冊的各級應試者已然可以享有部分權益,享有在特殊儀式、社交禮節、法律程序、賦稅徭役等方面范圍頗廣且程度不等的特權。
明代最早具有全國性影響的濟寧士紳是靳學顏和于若瀛。明代后期,濟寧的徐標成為當地士紳的榜樣。清代,濟寧玉堂孫家是山東最顯赫的家族之一。孫家的祖先在明初由山西洪洞遷移到山東西部的夏津,后來搬到濟寧。孫玉庭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獲得進士,在長達四十年的官宦生涯里擔任過高官,如兩江總督、體仁閣大學士等。他的長子孫善寶也曾擔任兩江總督,三子孫瑞珍官至禮部尚書和工部尚書。接下來,孫玉庭的六個孫輩都考中了進士,并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其中,孫毓溎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狀元,曾擔任省級高官。孫毓汶在咸豐六年(1856年)的進士考試中高中榜眼,并在19世紀末的晚清政局中位高權重,曾擔任軍機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要職,是受慈禧倚重的“后黨”。
可見,從明中葉到20世紀初,濟寧一直存在著強大而相對穩定的士紳階層,其中有許多經久不衰的大姓豪族起到支柱作用。正是他們在科舉考試、財富積累、社交網絡、地方社會活動中的持續成功,使這些士紳精英家族的江湖地位得以延續。同時,這些地方精英家庭交往頻繁,通過婚姻、文學結社、參與公共工程形成同盟。
濟寧的大多數城市士紳,都是在四鄉、周鄰地區擁有土地的城居地主,要么將土地出租給佃戶,要么派家人或代理人來管理農業。然而,與只重視田畝的北方士紳流行形象不同,濟寧士紳更加樂于參與城鎮市場活動。如此一來,商人也擠進了精英圈子,促使了“士紳—商人”復合體的形成。
孫家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在18至19世紀,孫家擁有超過3萬畝農田,并經營著名的玉堂醬園。商品化農業或商業中的家族產業收入,使得士紳精英能夠擴大其土地所有權,展示了士紳地主的傳統形象。其家庭成員在科舉考試和官宦生涯的成功,也為家族的商業事業提供了諸多利好。
在《經營地方》看來,富有的商人與士紳的耦合,促成了官、紳、商一體化。濟寧的這種情形與江南相似,而在北方卻不甚普遍。濟寧的地方志多次記錄了富裕和有教養的捐助者在地方公共項目中的巨額花費,并將“商”與“官”“紳”相提并論。
具體說來,濟寧士紳主導著當地的教育事業,建立眾多書院,與官方機構和機制相輔相成。此外,他們在社會福利事業上的貢獻,尤為普遍、深刻地影響著大眾生活。士紳通過捐資、督導和管理棲流所、養濟院、普濟堂、育嬰堂、留養局、義冢、粥廠等常設的或臨時的非政府機構,成為政府的合作者和代理人,在維護地方社會的日常運轉和應急防變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而非僅僅是輔助的作用。
精英的“能動性”
隨著運河設施的敗落、漕運的中斷、清朝中央集權的式微、東部沿海以西方因素為導引的工商業的崛起和擴張,清朝晚期,整個北方內陸運河地區急劇衰退。然而,與臨清等城市的命運不同,濟寧并沒有完全沒落。
溝通南北的大運河中斷后,濟寧段的運河水資源仍十分豐富,足以支持局部性船運。事實上,濟寧南抵江蘇北部的運道一直暢通。因此,濟寧的地方經濟雖然失去了廣闊延展的契機,但尚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往來循環。在南北鐵路大動脈及現代公路出現前,濟寧段的運河仍是貨運最主要的通道。
鑒于因運河而興的歷史經驗,濟寧士紳精英們認識到新式運輸業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從天津到浦口的長達1013公里的津浦鐵路,在1908年7月動工,1911年11月竣工,其中有420公里的路段經過山東。德國由于享有開采鐵路沿線礦產的特權,迫使線路經過礦脈豐富的曲阜、滋陽城(兗州府府治、今濟寧市兗州區)和鄒縣一帶,而這個方案忽略了長期作為區域中心的濟寧。從1907年開始,濟寧士紳和本籍京官竭盡所能爭取鐵路過境。雖然主干線未能改道,但是在1912年,穿過濟寧的兗州—濟寧支線與津浦干線得以同時通車,隨后不久,通過濟寧的貨運量每日可達700到800噸。濟寧火車站附近的新興市場,很快成為山東西南地區的貨物集散中心。
由于運河水道可以南達江蘇,加之江南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絡,濟寧繼續保持著與長江中下游的經濟聯系。由于鐵路的作用,濟寧與正在迅速崛起的沿海城市天津、青島、煙臺的商業和社會聯系得以加強。
孫競昊教授注意到,清亡后的十年中,濟寧地方精英的角色有一個明顯變化,即一些歸國留學生和新式教育畢業生開始出現。與此同時,新興的“市民”或城市職業者開始進入公共事務的領域。此外,規模龐大的民國官僚機構產生了一批現代公職人員,城市里出現了各種組織、協會。這些機構為地方精英們提供了平臺,精英們得以齊聚一堂,并決定一系列地方或行業事務。他們有效地組織了社會和政治活動,如禁止鴉片走私和吸食的宣傳、收回利權運動、學生抗議以及反對纏足、爭取平權教育的女性運動等。
《經營地方》認為,與通商口岸不同,濟寧這座內陸城市展現出了更具有中國色彩的現代化嘗試。這里沒有西方人的直接或壓倒性介入,展現出一條獨特的、中國內陸相對自主性的城市化道路。作為面臨衰落的運河城市,濟寧頑韌、有效的抵拒,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精英和居民的“能動性”。盡管不同團體和個人的目的與利益不盡一致,但是他們歡迎工業化和現代制度化教育,也盡可能保持地方和中國本土文化傳統。這種選擇根植于其自身悠久的文化遺產,深刻地影響到當地的現代化歷程。
從某種意義上看,將“濟寧經驗”中所提煉出的地方主義提升到理論分析的層面,可以推進對地方社會形態與國家政治權力機制之間關系的審視和思考,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
在新疆舍己救人的山東漢子魂歸故里
- 記者李旭旭8月18日,在新疆庫爾勒市,來自濰坊坊子區九龍街道王家屯村53歲的楊傳義因救一名13歲落水少年不幸遇難。25日,楊傳義的兒子楊新彬帶...[詳細]
- 齊魯晚報 2023-08-26
濟寧援疆助力生態游 英吉沙農家樂升級
- 本報英吉沙訊濟寧援疆指揮部、英吉沙縣借助豐厚的文化底蘊、獨特的風俗民情、精彩的非遺表演,吸引了疆內外大批游客。在精品旅游路線的帶動...[詳細]
- 濟寧日報 2023-08-26
山東省器械檢驗院獲批籌建醫療器械包裝標準化技術歸口單位
- 近日,由山東省醫療器械和藥品包裝檢驗研究院作為秘書處承擔單位的醫療器械包裝標準化技術歸口單位,經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籌建。這是省...[詳細]
- 齊魯壹點客戶端 2023-08-26
煙臺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關于規范全市食用鹽等相關商品價格行為的提醒告誡函
- 全市食用鹽等相關商品生產經營者 受“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排放入海”消息的影響,我市可能出現食用鹽等民生用品、核污染檢測儀器等相關商...[詳細]
- 膠東在線 2023-08-26
煙臺開發園區供電中心:小小窗口優質服務潤民心
- 膠東在線8月25日訊立秋后的太陽,絲毫沒有削減它的熱情。8月中旬正是每月的電費繳納高峰期,省級青年文明號開發園區供電中心營業廳剛開門不...[詳細]
- 膠東在線 2023-08-26
濟南市公安局起步區分局深化主動警務 護航重點項目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作為護航轄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軍,濟南市公安局起步區分局堅持“項目為王”理念,緊緊圍繞人民群眾和企業“...[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截至今年上半年,青島市公證機構累計辦理不動產登記業務3萬多筆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記者從發布會上獲悉,青島市司...[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濟南共辦理“帶押過戶”5109件,交易總額達93.82億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會上,濟南市司法局黨委書記、...[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青島市公證行業強化便民利民導向 推出精細化、貼心化服務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青島市司法局副局長劉春穎介紹...[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2022年以來,山東共辦理公證法律援助事項4600余件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山東省司法廳政治部主任、新聞...[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2019年以來,山東公證機構共辦理各類司法輔助案件65.7萬件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記者從發布會上獲悉,司法輔助...[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山東省公安廳:以檢視整改實績實效 推動主題教育走深走實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主題教育開展以來,山東省公安廳堅持問題導向,充分發揚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邊學習、邊對照、邊檢視、邊整改...[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
今年上半年,山東共辦理公證業務37.9萬件
- 中國山東網-感知山東8月25日訊8月25日,山東省政府新聞辦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山東省公證便民服務有關情況。記者從發布會上獲悉,山東是公...[詳細]
- 中國山東網 2023-08-26